
 云峰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0.8万
云峰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0.8万
晏临霄蹲在酸枝木茶台前,指尖捻着枚生锈的铜钱在烛火上翻烤。檀香混着普洱的陈味在古董店里浮沉,玻璃柜台里错落摆着几尊鎏金佛像,日光斜斜切过门楣,将"玄枢斋"的匾额映得半明半暗。 "晏老板,您给掌掌眼?"穿条纹polo衫的中年男人抹了把额头的汗,从公文包里掏出个红绸包裹。绸布揭开时带起细微的铜腥味,晏临霄眉梢微动,余光瞥见那枚双鱼玉佩沁着层诡异的青晕。 铜钱在烛焰里发出"滋"的轻响,晏临霄突然松手,看着烧红的钱币坠入茶海。水汽蒸腾间,男人手边的普洱泛起细密涟漪。"黄泉渡,阴阳错。"他拎起紫砂壶续茶,壶嘴悬在杯口三寸处顿住,“王先生最近…常做溺水的梦吧?”

 千年一剑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5.7万
千年一剑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5.7万
林分握着鸡毛掸子扫过博古架时,木雕貔貅突然翻了个跟头。八月的蝉鸣混着朝天门古玩市场的喧闹涌进小店,老式吊扇在头顶发出苟延残喘的吱呀声。 "见鬼了?"他伸手去扶那尊清代木雕,指尖刚触到包浆温润的雕工,柜台上的招财猫突然"啪嗒"一声摔了个倒栽葱。玻璃珠做的猫眼在水泥地上骨碌碌滚到门槛边,正巧被刚进门的胖子踩个正着。 "林子!你丫又在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?"王铁柱拎着两杯奶茶踉跄站稳,圆脸上还挂着空调房带出来的汗珠,“我妈让你今晚去家里吃火锅,说是给你驱驱邪气。”

 清虚道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4万
清虚道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4万
秦岭山区的暴雨来得毫无征兆。 黄豆大的雨点砸在越野车顶棚上,发出密集的鼓点声。林砚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发紧,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疯狂摆动,却怎么也擦不净瀑布般倾泻的雨水。后视镜里,考古队的白色面包车像只笨拙的甲壳虫,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挪动。 林砚原本是个考古专业的普通学生,原本以为假如真正的考古队还需要很长时间,但是一周之前,推荐他进入考古专业的老前辈却突然来找他,将他引荐给了考古地负责人。

 玄念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6万
玄念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6万
林忘尘蹲在宠物美容室的玻璃门前,食指和中指夹着的烟灰已经积了半寸长。他歪着头看笼子里那只正在啃磨牙棒的柯基犬,突然咧嘴一笑:“胖墩儿,你屁股这么圆,要是做成驴肉火烧能切八片不?” 柯基犬的磨牙棒"啪嗒"掉在笼底。 "小林!"店长从二楼探出头,地中海发型在吊灯下泛着油光,“给雪纳瑞剪指甲的客人等半小时了!”

 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08万
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08万
沈墨蹲在客栈二楼的木栏杆前,指尖的烟灰簌簌落在青苔斑驳的石阶上。远处群山在暮色中化作起伏的兽脊,山坳里飘荡的雾气正悄悄漫过青石板路,将檐角挂着的铜铃笼上一层惨白。这是他们被困在落魂坡的第三天。 木质楼梯突然传来密集的脚步声。穿着靛蓝布衫的客栈老板端着油灯上来,昏黄的光晕在他脸上割裂出深浅不一的阴影,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直勾勾盯着走廊尽头的客房——三天前考古队的四个学生就住在那间屋子。

 弥鹿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3万
弥鹿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3万
风云晨蹲在发霉的墙根下啃辣条,手机支架上的补光灯把泛黄的墙纸照得像块风干的腊肉。弹幕里飘过一片"主播又躲着吃独食",他对着镜头咧开沾着辣椒油的嘴:“家人们别急,等会儿这间凶宅要是真闹鬼,我把厉鬼的肠子掏出来涮火锅。” 手机突然发出刺耳的电流声,补光灯"啪"地炸成碎片。风云晨的后脖颈像被冰锥刺中,耳畔传来细碎的笑声,像是有人用指甲在挠黑板。他猛地转身,阴阳眼在黑暗中泛起幽绿的光——斑驳的墙面上渗出暗红色液体,蜿蜒成三个歪歪扭扭的血字:滚出去。

 三江鱼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9.9万
三江鱼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9.9万
腊月里的东北老街飘着细雪,铁皮招牌在寒风中哐当作响。林九安裹着军大衣蹲在门槛上剥蒜,脚边炭盆里飘起的灰烬混着纸钱碎屑,给"九安堂"的破木匾额蒙了层阴间滤镜。 “林哥!林哥救命啊!” 带着哭腔的尖叫惊得林九安手一抖,蒜瓣骨碌碌滚进雪堆。抬眼就见实习记者苏晓晓抱着个破布包冲过来,羽绒服帽子上还挂着半截黄裱纸,活像从坟堆里爬出来的傻狍子。

 云峰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1万
云峰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1万
湘西的夏夜闷热得能把人蒸熟,辰阳蹲在油腻腻的大排档塑料凳上,手指捏着啤酒瓶口转圈。霓虹灯管在雾气里晕成红绿光斑,隔壁桌划拳声混着炒田螺的香气,辣得他鼻腔发痒。 "阳子,最后喝一杯。"老猫把半杯白酒推过来,刀疤从右眼角斜劈到下巴,在油烟里泛着青紫。这四十岁的土夫子头子总爱穿件发黄的老头汗衫,胸口绣的"出入平安"都脱了线。

 老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4万
老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4万
江南的梅雨缠人得紧,晏潮声在茶色玻璃窗上呵出一团白雾,看着外头青石板路上撑油纸伞的行人像游魂般飘过。红泥小炭炉上的铜壶突突冒着热气,水雾在木梁间蜿蜒成蛇形。 “您就是晏先生?” 来人裹着腥湿的潮气跌坐在对面藤椅上。四十岁上下,鬓角染着灰白,深褐色夹克前襟沾着几点暗红,像是干涸的血迹。晏潮声的视线在他右手指甲缝停留片刻——那里嵌着棺底才有的朱砂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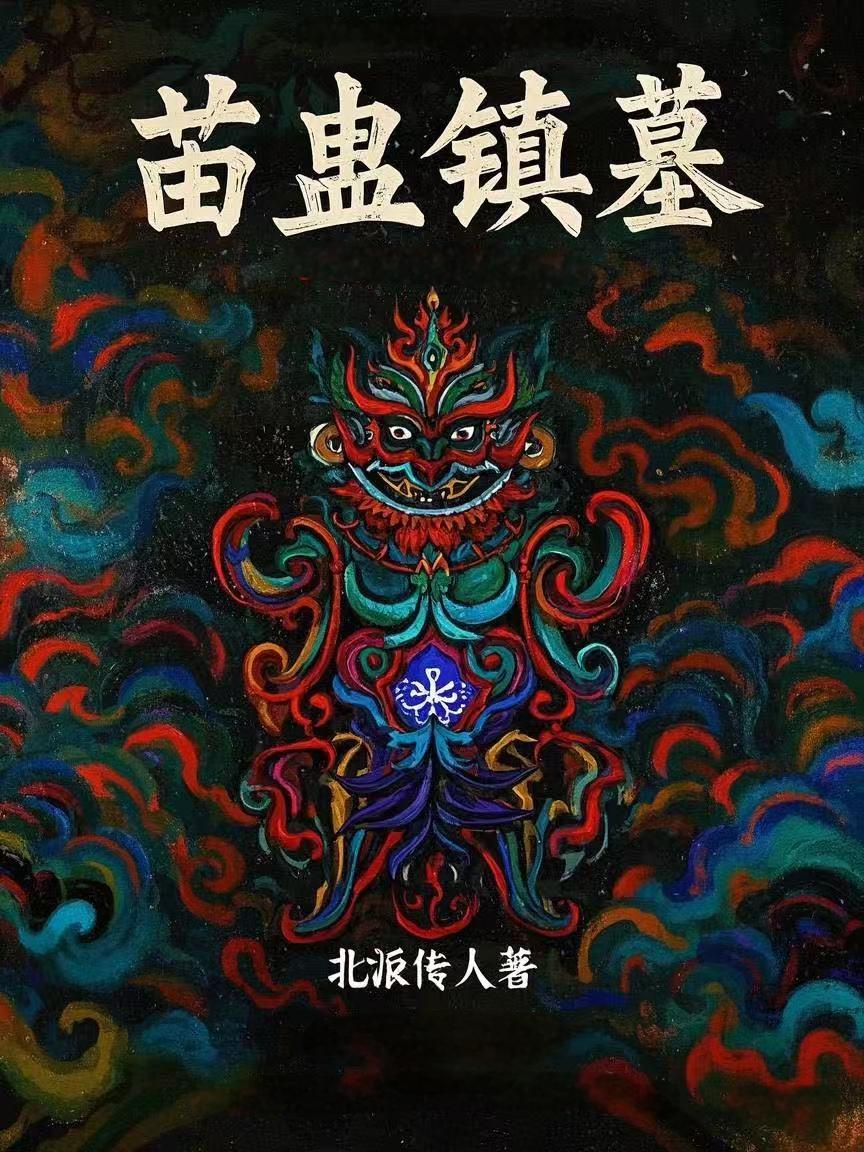
 北派传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1万
北派传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1万
残阳如血,将"腾天阁"褪色的金字招牌染成暗褐色。成天蹲在门槛上抽烟,青灰色烟雾缠绕着门楣悬挂的六角铜铃。这是第七根红塔山,烟灰缸里歪斜的烟蒂像插在坟头的香。 玻璃柜台上趴着只三花猫,突然炸毛跳起,碰翻了镇纸用的青铜玄武。成天伸手去接,指尖刚触到冰凉的龟甲,门口铜铃突然发疯似的摇晃。叮铃——叮铃叮铃——声音尖锐得像是有人在拿指甲刮玻璃。 “老板,买纸钱。”

 风流大官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4.6万
风流大官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4.6万
1953年的内蒙古戈壁,暮色像掺了沙子的血水漫过天际。冉风尘解开羊皮水囊的手突然顿住,指节在暮色中泛着玉器般的冷光。他仰头望着逐渐清晰的月亮,喉结滚动时脖颈上青色的九尾符咒纹路如同活物般游走。 "又到十五了。"他低声自语,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的古琴弦。 三十里外的心儿突然勒住缰绳,枣红马不安地刨着蹄子。她掏出怀里的青铜罗盘,看着指针疯狂旋转后直指西北。月光下少女的眉眼笼着层薄霜,羊皮袄里藏着的符纸簌簌作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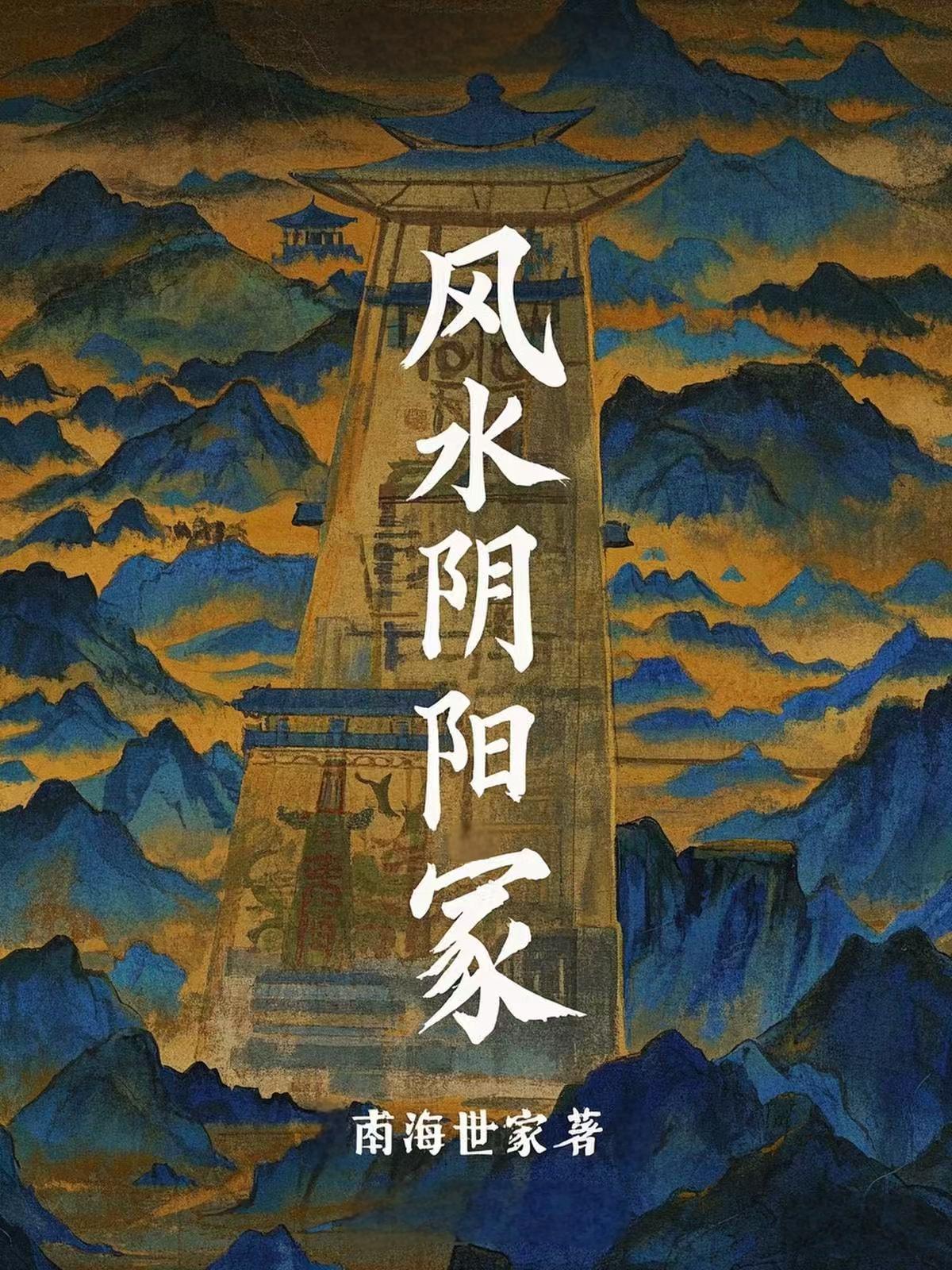
 南海世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7万
南海世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7万
夏夜的风裹着烧烤油烟掠过古城夜市,珩云蹲在塑料凳上嗦螺蛳粉,后颈突然炸起一片鸡皮疙瘩。三米开外的糖水摊前,穿黑西装的男人正用牙签扎破糯米糍,糖霜簌簌落进掌心。 "操,又是这帮孙子。"他猛灌一口冰豆浆,油汪汪的筷子精准戳中碗底的炸蛋。七个西装男呈扇形围拢,为首的正是在墓里被他用洛阳铲敲掉门牙的刀疤脸。 刀疤脸咧嘴露出镶金的牙:“珩老板,我们赵总请您喝茶。”

 贪婪的土豆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9.9万
贪婪的土豆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9.9万
言晶踩着七厘米的细高跟踏进别墅时,水晶吊灯忽然发出"噼啪"的电流声。她仰头望着晃动的灯穗,余光瞥见玄关处的貔貅摆件不知何时转向了东南方。 "言总,这位就是苏晨先生。"秘书小唐殷勤地引着个穿月白唐装的男人过来,那人指尖转着枚铜钱,在满屋子黑压压的丧服里活像只误入鸦群的丹顶鹤。 苏晨的丹凤眼扫过言晶锁骨间的翡翠平安扣,铜钱"叮"地弹向天花板。当那枚康熙通宝打着旋儿落回掌心时,他眉梢微不可察地跳了跳——卦象显示,这栋造价八千万的别墅,此刻正被某种活人忌煞笼罩着。

 草原孤狼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1.3万
草原孤狼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1.3万
我叫陆小天,是个抬棺材的。 这个职业可能很少有人了解。 从小到大,我都跟着爷爷一起做这个行当。 跟这些神鬼之事打交道,总是会遇到鬼,走夜路多了还能遇到鬼呢。 我又一次从梦中惊醒,想起了当年爷爷去世的时候,遇到的那些诡异的事情。 就算是到了现在,我也永生难忘,历历在目。 那天,爷爷刚出去给别人抬过了棺材,回来之后,突然就一头栽倒在地上,一病不起。

 九堡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6万
九堡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6万
冬夜的寒风呼啸,程仲缩了缩脖子,将衣服裹紧了一些,虎舍特有的腥臊味钻进鼻腔,程仲把最后一块鲜牛肉抛进铁笼,东北虎"大金"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,锋利的犬齿在月光下泛着寒光。 他是一名动物饲养员,已经做了快十年,一开始做是因为喜欢动物,但没有人知道的是,他有一种能够与动物沟通的特殊能力。

 北冥有鲲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15.9万
北冥有鲲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15.9万
杭州的秋雨下得绵密,周谨言站在西泠印社旁的古董店二楼,指尖刚触到雕花木窗,一道惊雷突然劈开浓稠的夜色。玻璃窗上蜿蜒的水痕被闪电映得发亮,像无数条扭动的银蛇。 楼下传来三声闷响,不轻不重地扣在包铜木门上。他看了眼座钟,十一点零三分,这个时辰不该有客。转身时踢翻了青瓷笔洗,墨汁泼在波斯地毯上晕开狰狞的暗影。

 六斤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7.9万
六斤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7.9万
1925年秋,上海霞飞路的梧桐叶在暮色里簌簌作响。乔砚之裹紧灰呢大衣穿过街角,皮鞋踏碎霓虹倒影里的西洋广告画。街边报童挥着《申报》叫嚷日本纱厂罢工的消息,黄包车夫骂骂咧咧地撞开卖糖炒栗子的摊子,空气里浮着鸦片烟与雪花膏混杂的浊气。 "乔先生!"穿香云纱的茶楼伙计追上来,袖口沾着墨迹,“您订的《泰晤士报》到了,今早刚到的伦敦船货。”

 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6万
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6万
北风卷着雪粒子抽打窗棂,陆预缩在灶台前烤火,后脖颈突然挨了一记鞋底。父亲陆永贵佝偻着腰站在门口,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清单,棉袄上沾着棺木刨花的碎屑。 "小兔崽子就知道躲懒!"老棺材匠把纸条甩在儿子脸上,“赶紧去镇上置办五色纸钱、引魂幡,再捎两坛高粱烧回来。老孙头家明儿出殡,棺材还差最后三道漆。”

 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5.1万
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5.1万
鹧毅蹲在米仓角落,指尖掠过青砖缝隙里的陈年糯米。月光透过雕花木窗斜切进来,在堆满麻袋的阴影里割出一道惨白的裂痕。 鹧毅的父亲是搬山道人,家里开米行为生,自从父亲失踪之后鹧毅渐渐的已经听不到关于父亲的传说,虽然他已将父亲的衣钵学成了九成,可一直没有等到父亲归家的鹧毅,却已对那些渐渐失去了兴趣。 思索间,米行后门的铜铃叮当突然乱响,那串父亲生前亲手挂的铃铛,此刻震得像是要把整条西大街都惊醒。

 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7.9万
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7.9万
1946年5月的哈尔滨还带着料峭春寒,秦颂握着军用水壶的手指节发白。卡车在泥泞山路上颠簸,后车厢里消毒水与血腥味混杂,程菲正在给昏厥的战士换药。 日军刚刚撤出哈尔滨,秦颂临危受命,必须找到731的试验根据地,找到日军藏起来的细菌实验标本。 "还有半小时就到平房区。"他望着远处墨色山峦,那些传说中活人进去就再没出来的原始老林,此刻在暮色里像蹲伏的巨兽。车斗里突然传来金属碰撞声,苏聪的医药箱被颠开,针管滚到沾满泥浆的帆布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