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清虚道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4万
清虚道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4万
秦岭山区的暴雨来得毫无征兆。 黄豆大的雨点砸在越野车顶棚上,发出密集的鼓点声。林砚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发紧,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疯狂摆动,却怎么也擦不净瀑布般倾泻的雨水。后视镜里,考古队的白色面包车像只笨拙的甲壳虫,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挪动。 林砚原本是个考古专业的普通学生,原本以为假如真正的考古队还需要很长时间,但是一周之前,推荐他进入考古专业的老前辈却突然来找他,将他引荐给了考古地负责人。

 玄念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6万
玄念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6万
林忘尘蹲在宠物美容室的玻璃门前,食指和中指夹着的烟灰已经积了半寸长。他歪着头看笼子里那只正在啃磨牙棒的柯基犬,突然咧嘴一笑:“胖墩儿,你屁股这么圆,要是做成驴肉火烧能切八片不?” 柯基犬的磨牙棒"啪嗒"掉在笼底。 "小林!"店长从二楼探出头,地中海发型在吊灯下泛着油光,“给雪纳瑞剪指甲的客人等半小时了!”

 弥鹿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3万
弥鹿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3万
风云晨蹲在发霉的墙根下啃辣条,手机支架上的补光灯把泛黄的墙纸照得像块风干的腊肉。弹幕里飘过一片"主播又躲着吃独食",他对着镜头咧开沾着辣椒油的嘴:“家人们别急,等会儿这间凶宅要是真闹鬼,我把厉鬼的肠子掏出来涮火锅。” 手机突然发出刺耳的电流声,补光灯"啪"地炸成碎片。风云晨的后脖颈像被冰锥刺中,耳畔传来细碎的笑声,像是有人用指甲在挠黑板。他猛地转身,阴阳眼在黑暗中泛起幽绿的光——斑驳的墙面上渗出暗红色液体,蜿蜒成三个歪歪扭扭的血字:滚出去。

 三江鱼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9.9万
三江鱼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9.9万
腊月里的东北老街飘着细雪,铁皮招牌在寒风中哐当作响。林九安裹着军大衣蹲在门槛上剥蒜,脚边炭盆里飘起的灰烬混着纸钱碎屑,给"九安堂"的破木匾额蒙了层阴间滤镜。 “林哥!林哥救命啊!” 带着哭腔的尖叫惊得林九安手一抖,蒜瓣骨碌碌滚进雪堆。抬眼就见实习记者苏晓晓抱着个破布包冲过来,羽绒服帽子上还挂着半截黄裱纸,活像从坟堆里爬出来的傻狍子。

 云峰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1万
云峰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1万
湘西的夏夜闷热得能把人蒸熟,辰阳蹲在油腻腻的大排档塑料凳上,手指捏着啤酒瓶口转圈。霓虹灯管在雾气里晕成红绿光斑,隔壁桌划拳声混着炒田螺的香气,辣得他鼻腔发痒。 "阳子,最后喝一杯。"老猫把半杯白酒推过来,刀疤从右眼角斜劈到下巴,在油烟里泛着青紫。这四十岁的土夫子头子总爱穿件发黄的老头汗衫,胸口绣的"出入平安"都脱了线。

 老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4万
老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4万
江南的梅雨缠人得紧,晏潮声在茶色玻璃窗上呵出一团白雾,看着外头青石板路上撑油纸伞的行人像游魂般飘过。红泥小炭炉上的铜壶突突冒着热气,水雾在木梁间蜿蜒成蛇形。 “您就是晏先生?” 来人裹着腥湿的潮气跌坐在对面藤椅上。四十岁上下,鬓角染着灰白,深褐色夹克前襟沾着几点暗红,像是干涸的血迹。晏潮声的视线在他右手指甲缝停留片刻——那里嵌着棺底才有的朱砂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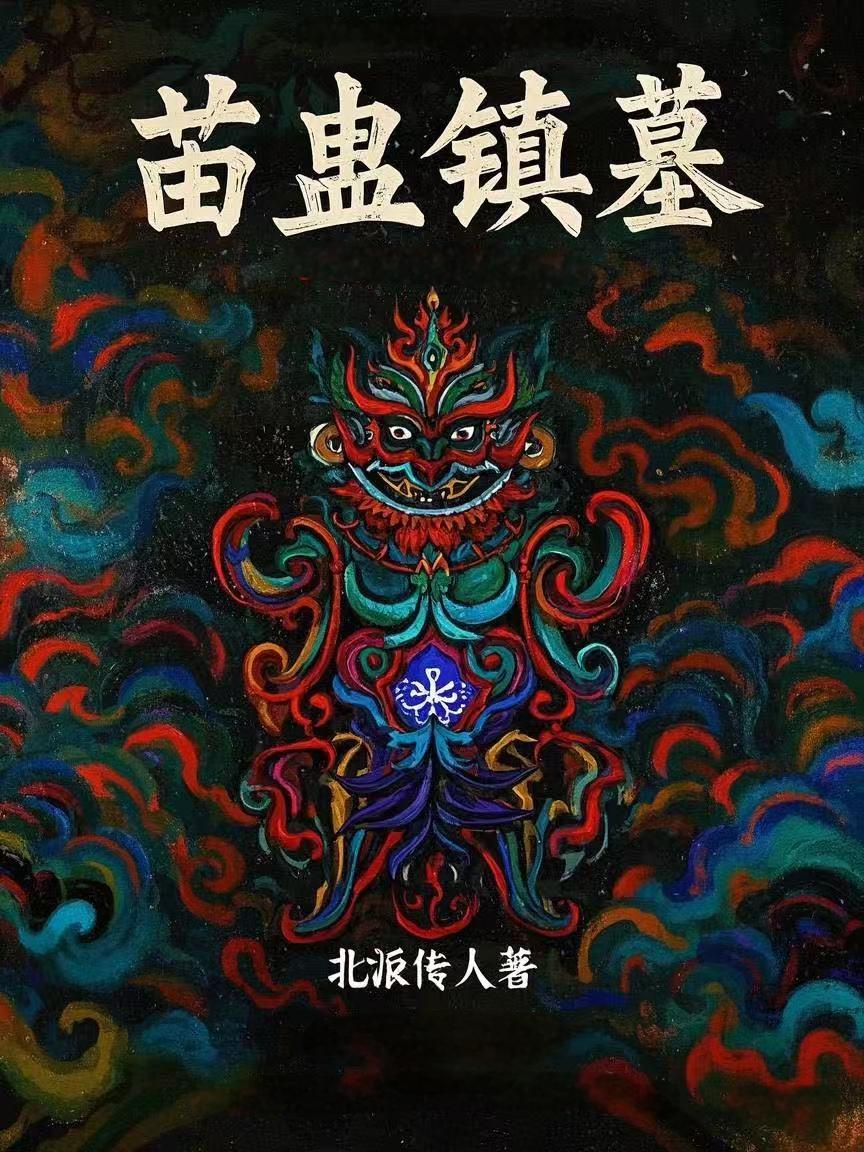
 北派传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1万
北派传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1万
残阳如血,将"腾天阁"褪色的金字招牌染成暗褐色。成天蹲在门槛上抽烟,青灰色烟雾缠绕着门楣悬挂的六角铜铃。这是第七根红塔山,烟灰缸里歪斜的烟蒂像插在坟头的香。 玻璃柜台上趴着只三花猫,突然炸毛跳起,碰翻了镇纸用的青铜玄武。成天伸手去接,指尖刚触到冰凉的龟甲,门口铜铃突然发疯似的摇晃。叮铃——叮铃叮铃——声音尖锐得像是有人在拿指甲刮玻璃。 “老板,买纸钱。”

 风流大官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4.6万
风流大官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4.6万
1953年的内蒙古戈壁,暮色像掺了沙子的血水漫过天际。冉风尘解开羊皮水囊的手突然顿住,指节在暮色中泛着玉器般的冷光。他仰头望着逐渐清晰的月亮,喉结滚动时脖颈上青色的九尾符咒纹路如同活物般游走。 "又到十五了。"他低声自语,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的古琴弦。 三十里外的心儿突然勒住缰绳,枣红马不安地刨着蹄子。她掏出怀里的青铜罗盘,看着指针疯狂旋转后直指西北。月光下少女的眉眼笼着层薄霜,羊皮袄里藏着的符纸簌簌作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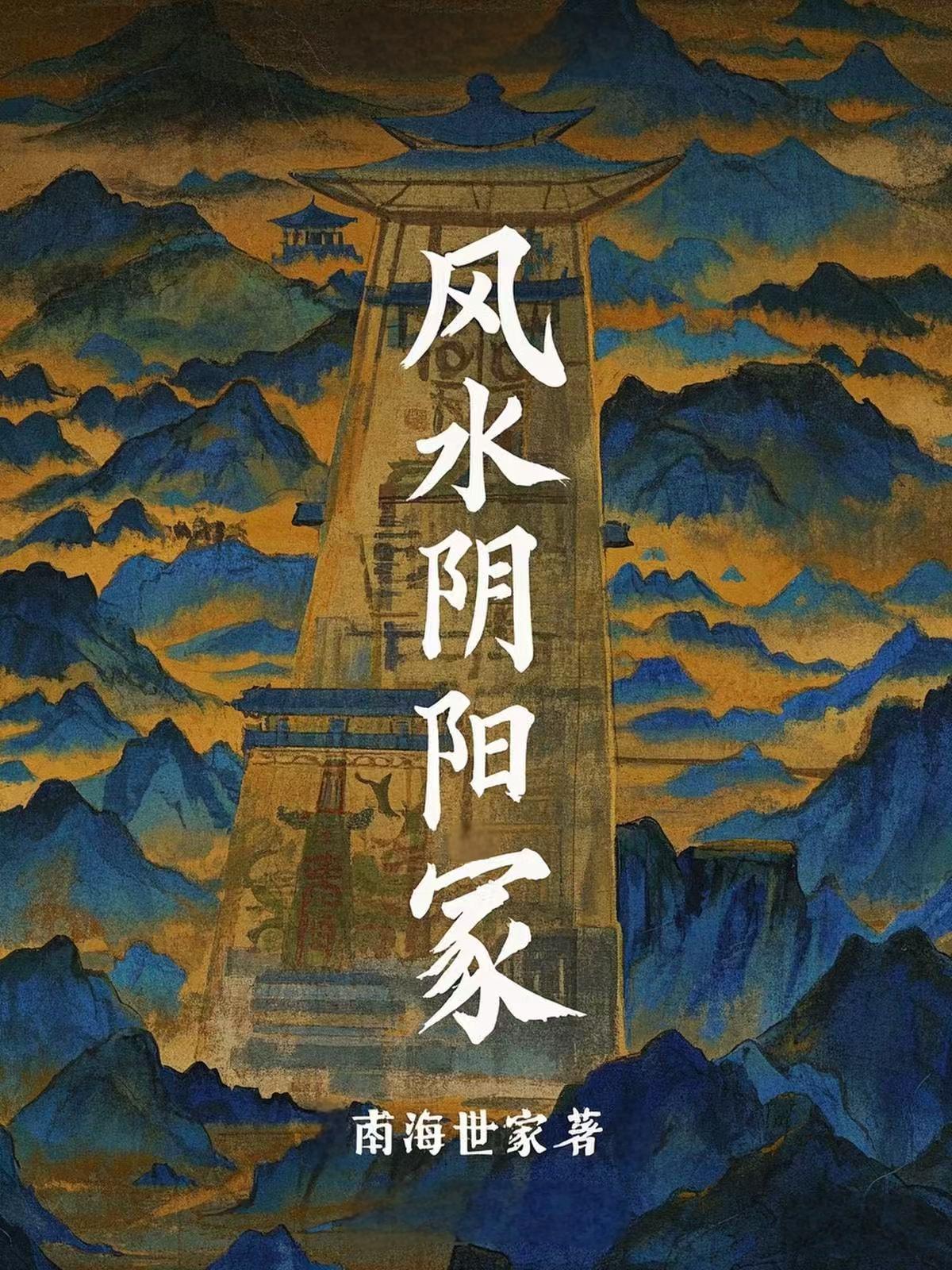
 南海世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7万
南海世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7万
夏夜的风裹着烧烤油烟掠过古城夜市,珩云蹲在塑料凳上嗦螺蛳粉,后颈突然炸起一片鸡皮疙瘩。三米开外的糖水摊前,穿黑西装的男人正用牙签扎破糯米糍,糖霜簌簌落进掌心。 "操,又是这帮孙子。"他猛灌一口冰豆浆,油汪汪的筷子精准戳中碗底的炸蛋。七个西装男呈扇形围拢,为首的正是在墓里被他用洛阳铲敲掉门牙的刀疤脸。 刀疤脸咧嘴露出镶金的牙:“珩老板,我们赵总请您喝茶。”

 贪婪的土豆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9.9万
贪婪的土豆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9.9万
言晶踩着七厘米的细高跟踏进别墅时,水晶吊灯忽然发出"噼啪"的电流声。她仰头望着晃动的灯穗,余光瞥见玄关处的貔貅摆件不知何时转向了东南方。 "言总,这位就是苏晨先生。"秘书小唐殷勤地引着个穿月白唐装的男人过来,那人指尖转着枚铜钱,在满屋子黑压压的丧服里活像只误入鸦群的丹顶鹤。 苏晨的丹凤眼扫过言晶锁骨间的翡翠平安扣,铜钱"叮"地弹向天花板。当那枚康熙通宝打着旋儿落回掌心时,他眉梢微不可察地跳了跳——卦象显示,这栋造价八千万的别墅,此刻正被某种活人忌煞笼罩着。

 九堡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6万
九堡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6万
冬夜的寒风呼啸,程仲缩了缩脖子,将衣服裹紧了一些,虎舍特有的腥臊味钻进鼻腔,程仲把最后一块鲜牛肉抛进铁笼,东北虎"大金"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,锋利的犬齿在月光下泛着寒光。 他是一名动物饲养员,已经做了快十年,一开始做是因为喜欢动物,但没有人知道的是,他有一种能够与动物沟通的特殊能力。

 河东河西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58.1万
河东河西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58.1万
梧桐巷的暮色来得特别早。 秦羽叼着半根油条蹲在门槛上,看最后一片夕阳从"雅藏轩"的鎏金牌匾上滑落。玻璃柜里那些青花瓷在暮色里泛着幽光,像一群沉默的观众。他打了个哈欠,后颈的纱布被晚风掀起一角——三天前那个混乱的夜,此刻还在隐隐作痛。 他抬手摸了摸头上的伤,为了生计不过是在古董店做个一个月拿两千块钱的小店员,凭什么自己要遭此横祸? 正为自己惋惜着,手机在裤兜里震起来,是老横发来的语音:“我说秦哥,真不用我陪你去医院复查?你后脑勺那伤看着就瘆人…”

 六斤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7.9万
六斤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7.9万
1925年秋,上海霞飞路的梧桐叶在暮色里簌簌作响。乔砚之裹紧灰呢大衣穿过街角,皮鞋踏碎霓虹倒影里的西洋广告画。街边报童挥着《申报》叫嚷日本纱厂罢工的消息,黄包车夫骂骂咧咧地撞开卖糖炒栗子的摊子,空气里浮着鸦片烟与雪花膏混杂的浊气。 "乔先生!"穿香云纱的茶楼伙计追上来,袖口沾着墨迹,“您订的《泰晤士报》到了,今早刚到的伦敦船货。”

 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6万
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6万
北风卷着雪粒子抽打窗棂,陆预缩在灶台前烤火,后脖颈突然挨了一记鞋底。父亲陆永贵佝偻着腰站在门口,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清单,棉袄上沾着棺木刨花的碎屑。 "小兔崽子就知道躲懒!"老棺材匠把纸条甩在儿子脸上,“赶紧去镇上置办五色纸钱、引魂幡,再捎两坛高粱烧回来。老孙头家明儿出殡,棺材还差最后三道漆。”

 黑色网格 |
都市娱乐 |
完本 |
60.8万
黑色网格 |
都市娱乐 |
完本 |
60.8万
潮湿的出租屋里,空调外机发出老旧的嗡鸣。 周燃盯着手机屏幕上跳动的消息提示,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发白。浴室里传来哗哗水声,磨砂玻璃映出苏雪玲珑的曲线,水珠顺着她抬起的手臂滑落,在暖黄灯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。 “叮——” 微信弹窗突然跳出置顶对话框,备注"宝贝雪儿"的聊天框里,最新消息是张衬衫半敞的腹肌照。周燃瞳孔猛地收缩,手指不受控制地往上滑动。

 安澜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85.2万
安澜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85.2万
青石广场上的晨雾还未散尽,林焰的掌心已经沁出一层薄汗。他盯着三丈高的测灵柱,喉结上下滚动——这已经是第三次尝试了。 "下品火灵根。"执事长老的声音像块冷铁砸在青砖上,四周传来压低的嗤笑。林焰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,他能清晰看见测灵柱底端那截暗红色纹路,像条蜷缩的蚯蚓,连第一道刻度都没能爬上去。 "看来咱们林家又要多个烧火工了。"背后传来林昊阴阳怪气的笑声,这位大长老的嫡孙故意晃了晃自己的中品水灵根,腰间玉佩撞得叮当作响。

 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5.1万
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5.1万
鹧毅蹲在米仓角落,指尖掠过青砖缝隙里的陈年糯米。月光透过雕花木窗斜切进来,在堆满麻袋的阴影里割出一道惨白的裂痕。 鹧毅的父亲是搬山道人,家里开米行为生,自从父亲失踪之后鹧毅渐渐的已经听不到关于父亲的传说,虽然他已将父亲的衣钵学成了九成,可一直没有等到父亲归家的鹧毅,却已对那些渐渐失去了兴趣。 思索间,米行后门的铜铃叮当突然乱响,那串父亲生前亲手挂的铃铛,此刻震得像是要把整条西大街都惊醒。

 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7.9万
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7.9万
1946年5月的哈尔滨还带着料峭春寒,秦颂握着军用水壶的手指节发白。卡车在泥泞山路上颠簸,后车厢里消毒水与血腥味混杂,程菲正在给昏厥的战士换药。 日军刚刚撤出哈尔滨,秦颂临危受命,必须找到731的试验根据地,找到日军藏起来的细菌实验标本。 "还有半小时就到平房区。"他望着远处墨色山峦,那些传说中活人进去就再没出来的原始老林,此刻在暮色里像蹲伏的巨兽。车斗里突然传来金属碰撞声,苏聪的医药箱被颠开,针管滚到沾满泥浆的帆布上。

 黑咖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81.4万
黑咖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81.4万
咸腥的海风裹着铁锈味灌进鼻腔,郑和扶住剧烈摇晃的桅杆,望着铅灰色天穹下翻涌的怒涛。第七次了,自宝船驶入满剌加海峡,这场妖风就像附骨之疽纠缠不休。 “轰!” 又一道惊雷劈在左舷三十丈处,靛蓝电光里隐约可见珊瑚礁狰狞的轮廓。王景弘跌跌撞撞冲上舵台,镶金蟒袍被雨水浸成深褐色:“郑大人!罗盘针又开始打转!”

 兆民 |
都市娱乐 |
完本 |
62.4万
兆民 |
都市娱乐 |
完本 |
62.4万
林小凡蹲在巷子口的垃圾箱后面,看着自己微微发抖的手掌,第108次确认这绝对不是在做梦。三分钟前他刚被张彪那伙人堵在学校后门,现在裤兜里突然多了块会说话的玉佩——准确来说,是这块雕着歪歪扭扭云纹的青玉挂坠,正用河南口音在他脑子里播放《好运来》。 "检测到宿主符合最低生存标准,天道补习班系统启动中…"玉佩突然正经起来的机械音吓得他差点咬到舌头。远处传来张彪骂骂咧咧的声音,林小凡把玉佩攥得更紧了些,后背紧贴着冰凉的砖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