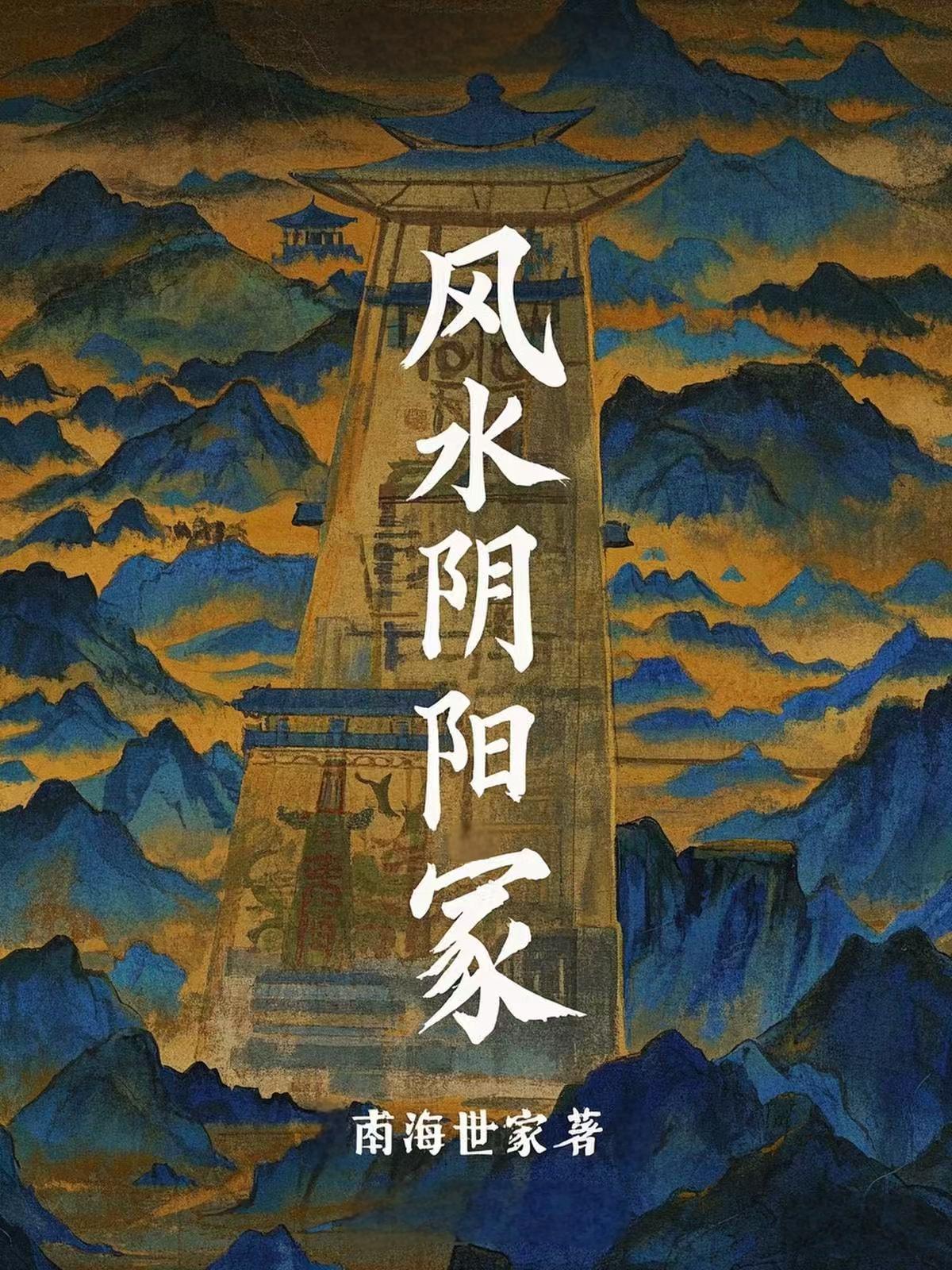
 南海世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7万
南海世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7万
夏夜的风裹着烧烤油烟掠过古城夜市,珩云蹲在塑料凳上嗦螺蛳粉,后颈突然炸起一片鸡皮疙瘩。三米开外的糖水摊前,穿黑西装的男人正用牙签扎破糯米糍,糖霜簌簌落进掌心。 "操,又是这帮孙子。"他猛灌一口冰豆浆,油汪汪的筷子精准戳中碗底的炸蛋。七个西装男呈扇形围拢,为首的正是在墓里被他用洛阳铲敲掉门牙的刀疤脸。 刀疤脸咧嘴露出镶金的牙:“珩老板,我们赵总请您喝茶。”

 贪婪的土豆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9.9万
贪婪的土豆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9.9万
言晶踩着七厘米的细高跟踏进别墅时,水晶吊灯忽然发出"噼啪"的电流声。她仰头望着晃动的灯穗,余光瞥见玄关处的貔貅摆件不知何时转向了东南方。 "言总,这位就是苏晨先生。"秘书小唐殷勤地引着个穿月白唐装的男人过来,那人指尖转着枚铜钱,在满屋子黑压压的丧服里活像只误入鸦群的丹顶鹤。 苏晨的丹凤眼扫过言晶锁骨间的翡翠平安扣,铜钱"叮"地弹向天花板。当那枚康熙通宝打着旋儿落回掌心时,他眉梢微不可察地跳了跳——卦象显示,这栋造价八千万的别墅,此刻正被某种活人忌煞笼罩着。

 草原孤狼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1.3万
草原孤狼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1.3万
我叫陆小天,是个抬棺材的。 这个职业可能很少有人了解。 从小到大,我都跟着爷爷一起做这个行当。 跟这些神鬼之事打交道,总是会遇到鬼,走夜路多了还能遇到鬼呢。 我又一次从梦中惊醒,想起了当年爷爷去世的时候,遇到的那些诡异的事情。 就算是到了现在,我也永生难忘,历历在目。 那天,爷爷刚出去给别人抬过了棺材,回来之后,突然就一头栽倒在地上,一病不起。

 山葵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1.9万
山葵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1.9万
市局专案组,为了维护这座城市的安宁,成立的一年多以来,命案必破有案必追,成为了A市的一把利刃。 带领专案组的组长苏文霖成为了明星刑警,带领着专案组众人屡破其案,然而现在,专案组的人却焦头烂额。 法医周然蹲在散发着腐臭的垃圾桶旁,橡胶手套上沾着黏腻的液体。警戒线外晨练的老头正对着记者镜头比划:“这小区二十年没出过命案,肯定是外来人…”

 九堡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6万
九堡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6万
冬夜的寒风呼啸,程仲缩了缩脖子,将衣服裹紧了一些,虎舍特有的腥臊味钻进鼻腔,程仲把最后一块鲜牛肉抛进铁笼,东北虎"大金"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,锋利的犬齿在月光下泛着寒光。 他是一名动物饲养员,已经做了快十年,一开始做是因为喜欢动物,但没有人知道的是,他有一种能够与动物沟通的特殊能力。

 随风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4.5万
随风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4.5万
灵堂里的长明灯忽然晃了晃。 三岁的苏倩文缩在阿爸的羊皮袄里,看着棺材底下渗出的水渍在青砖地上蜿蜒。那水透着股腥气,像是刚从冰窟窿里捞出来的鱼,在七月流火的夜里凝成细小的冰晶。 她的爸爸,是有名的棺材匠,手艺好人也老实,苏倩文在襁褓里就跟着他们出入各种白事,对这种环境早已习以为常。

 北冥有鲲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15.9万
北冥有鲲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15.9万
杭州的秋雨下得绵密,周谨言站在西泠印社旁的古董店二楼,指尖刚触到雕花木窗,一道惊雷突然劈开浓稠的夜色。玻璃窗上蜿蜒的水痕被闪电映得发亮,像无数条扭动的银蛇。 楼下传来三声闷响,不轻不重地扣在包铜木门上。他看了眼座钟,十一点零三分,这个时辰不该有客。转身时踢翻了青瓷笔洗,墨汁泼在波斯地毯上晕开狰狞的暗影。

 六斤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7.9万
六斤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7.9万
1925年秋,上海霞飞路的梧桐叶在暮色里簌簌作响。乔砚之裹紧灰呢大衣穿过街角,皮鞋踏碎霓虹倒影里的西洋广告画。街边报童挥着《申报》叫嚷日本纱厂罢工的消息,黄包车夫骂骂咧咧地撞开卖糖炒栗子的摊子,空气里浮着鸦片烟与雪花膏混杂的浊气。 "乔先生!"穿香云纱的茶楼伙计追上来,袖口沾着墨迹,“您订的《泰晤士报》到了,今早刚到的伦敦船货。”

 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6万
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6万
北风卷着雪粒子抽打窗棂,陆预缩在灶台前烤火,后脖颈突然挨了一记鞋底。父亲陆永贵佝偻着腰站在门口,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清单,棉袄上沾着棺木刨花的碎屑。 "小兔崽子就知道躲懒!"老棺材匠把纸条甩在儿子脸上,“赶紧去镇上置办五色纸钱、引魂幡,再捎两坛高粱烧回来。老孙头家明儿出殡,棺材还差最后三道漆。”

 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2.9万
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2.9万
雨丝在警戒线外织成银灰色帘幕,鹿珏转动着六阶魔方的手指突然停顿。警戒线内,穿着明黄色雨衣的鉴证人员像游动的萤火虫,在垃圾填埋场的腐臭中穿梭。她将魔方收进卡其色风衣口袋时,金属棱角硌到掌心尚未愈合的刀伤。 "组长,第三具了。"苏风风举着平板电脑凑过来,马尾辫扫过防毒面具边缘。屏幕上的三维建模图正在旋转,红点标注着三个抛尸点构成的等边三角形,“每次间隔十三天,这次是…”

 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2.4万
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2.4万
孟清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收紧,挡风玻璃上的雨刷以最高频率摆动,仍追不上鹅毛大雪的坠落速度。仪表盘显示室外温度零下十二度,车载广播里女主持人正用甜美的声音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出行。她瞥了眼副驾驶座上的银色工具箱,金属卡扣在颠簸中发出细碎碰撞声。 地下车库的感应灯随着轮胎碾压声次第亮起,在灰白墙面投下扭曲的光斑。孟清拎起工具箱推开车门,皮靴跟敲击水泥地的回声突兀地刺穿寂静。第三根承重柱后传来砂砾碾动的细响,她不动声色地加快脚步,工具箱底部的防滑纹路在掌心压出深痕。

 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5.1万
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5.1万
鹧毅蹲在米仓角落,指尖掠过青砖缝隙里的陈年糯米。月光透过雕花木窗斜切进来,在堆满麻袋的阴影里割出一道惨白的裂痕。 鹧毅的父亲是搬山道人,家里开米行为生,自从父亲失踪之后鹧毅渐渐的已经听不到关于父亲的传说,虽然他已将父亲的衣钵学成了九成,可一直没有等到父亲归家的鹧毅,却已对那些渐渐失去了兴趣。 思索间,米行后门的铜铃叮当突然乱响,那串父亲生前亲手挂的铃铛,此刻震得像是要把整条西大街都惊醒。

 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7.9万
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7.9万
1946年5月的哈尔滨还带着料峭春寒,秦颂握着军用水壶的手指节发白。卡车在泥泞山路上颠簸,后车厢里消毒水与血腥味混杂,程菲正在给昏厥的战士换药。 日军刚刚撤出哈尔滨,秦颂临危受命,必须找到731的试验根据地,找到日军藏起来的细菌实验标本。 "还有半小时就到平房区。"他望着远处墨色山峦,那些传说中活人进去就再没出来的原始老林,此刻在暮色里像蹲伏的巨兽。车斗里突然传来金属碰撞声,苏聪的医药箱被颠开,针管滚到沾满泥浆的帆布上。

 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4.7万
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4.7万
盛夏的暴雨砸在刑事法院的钢化玻璃幕墙上,苏文翔扯松领带第三次看向腕表。九点零七分,距离正式开庭还有二十三分钟,旁听席已经坐满举着长枪短炮的记者。 "苏律师,这是法医补充的毒理报告。"助理小跑着递上文件夹,“他们说死者体内检测出…”

 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3.2万
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3.2万
雨水在挡风玻璃上汇成细流,雨刮器以最大频率来回摆动,依然扫不净连绵的雨帘。苏逸抹了把后视镜上的水汽,看着镜中自己发梢滴水的模样,伸手将空调出风口掰到最大。潮湿的制服布料黏在后背,寒意顺着脊椎往上爬,像条冰冷的蛇。 “您有新的派送任务。” 手机导航机械音划破车内沉闷,苏逸瞥了眼屏幕。

 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5.6
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5.6
市局刑侦支队会议室的白炽灯亮得刺眼,陈飞将案件卷宗平铺在会议桌上,金属桌沿倒映着墙面的电子钟——6:47分。专案组第一次集结就赶上暴雨预警,走廊里传来年轻警员奔跑时带起的潮湿水汽。羊毛深处的秘密、暗室里的十字绣、氰化物、工伤报告、自动驾驶、地下车库、右手指纹、浇筑模板,所有的线索都只想谁?

 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3.4万
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3.4万
暮色像一滩凝固的墨迹,沿着梧桐树虬结的枝干缓缓晕染。沈桥把解剖报告往腋下夹紧了些,法医制服第三颗纽扣被秋风掀开缝隙,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蓝衬衫。银杏大道尽头的垃圾桶旁,外卖员正弯腰收拾撒落的餐盒,油渍在暮色中泛着暗红光泽,让她想起今早解剖台上那具溺亡尸体的手指。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三次,不用看都知道是母亲发来的养生文章。沈桥数着斑马线上第13块地砖——这是她维持了五年的强迫症——突然瞥见婚纱店橱窗倒影里自己苍白的脸。玻璃内侧模特穿着鱼尾拖尾婚纱,头纱边缘用金线绣着百合,和上周那个新娘尸体的装束如出一辙。

 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4.5万
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4.5万
审讯室的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电流声,袁冉看着面前这个第三次把保温杯转出半圈的男人。不锈钢杯底在铁质桌面划出尖锐声响,五十岁的汽车修理工张德发鬓角结着油垢,右手拇指神经质地摩挲着食指侧面的老茧。 "张师傅,您工具箱里那把24号梅花扳手上沾着三处血迹。"袁冉将物证照片推过桌面,指腹在塑封边缘留下月牙状压痕,“您说这是给隔壁老王修三轮车时蹭的鸡血?”

 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0.7万
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0.7万
沥青路面蒸腾着暑气,孟瑶推开车门时,黏稠的热浪裹着血腥味扑面而来。她站在警戒线外仰头望去,斑驳的"仁和医院"四个鎏金大字在烈日下泛着诡异的暗红色,像是被风干的陈旧血迹。 "孟队。"痕检科的老周提着工具箱迎上来,防护服领口洇着汗渍,“报案中心转过来的录音你听过了?”

 安慕希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1.7万
安慕希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1.7万
生物实验室的空调发出沉闷的嗡鸣,楚涧盯着解剖台上微微抽搐的牛蛙,粘稠的福尔马林气味裹着六月暑气黏在鼻腔里。讲台上周慕云教授的银丝眼镜泛着冷光,手术刀尖正沿着牛蛙鼓胀的腹部缓慢游走。 "当神经长期承受高压…"刀尖突然刺入,淡黄色组织液顺着不锈钢台面蜿蜒,前排女生捂住嘴干呕,"肌肉纤维会产生记忆性震颤。"那只牛蛙的后腿猛地蹬直,足蹼上的薄膜在无影灯下透出诡异的粉红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