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风流大官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4.6万
风流大官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4.6万
1953年的内蒙古戈壁,暮色像掺了沙子的血水漫过天际。冉风尘解开羊皮水囊的手突然顿住,指节在暮色中泛着玉器般的冷光。他仰头望着逐渐清晰的月亮,喉结滚动时脖颈上青色的九尾符咒纹路如同活物般游走。 "又到十五了。"他低声自语,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的古琴弦。 三十里外的心儿突然勒住缰绳,枣红马不安地刨着蹄子。她掏出怀里的青铜罗盘,看着指针疯狂旋转后直指西北。月光下少女的眉眼笼着层薄霜,羊皮袄里藏着的符纸簌簌作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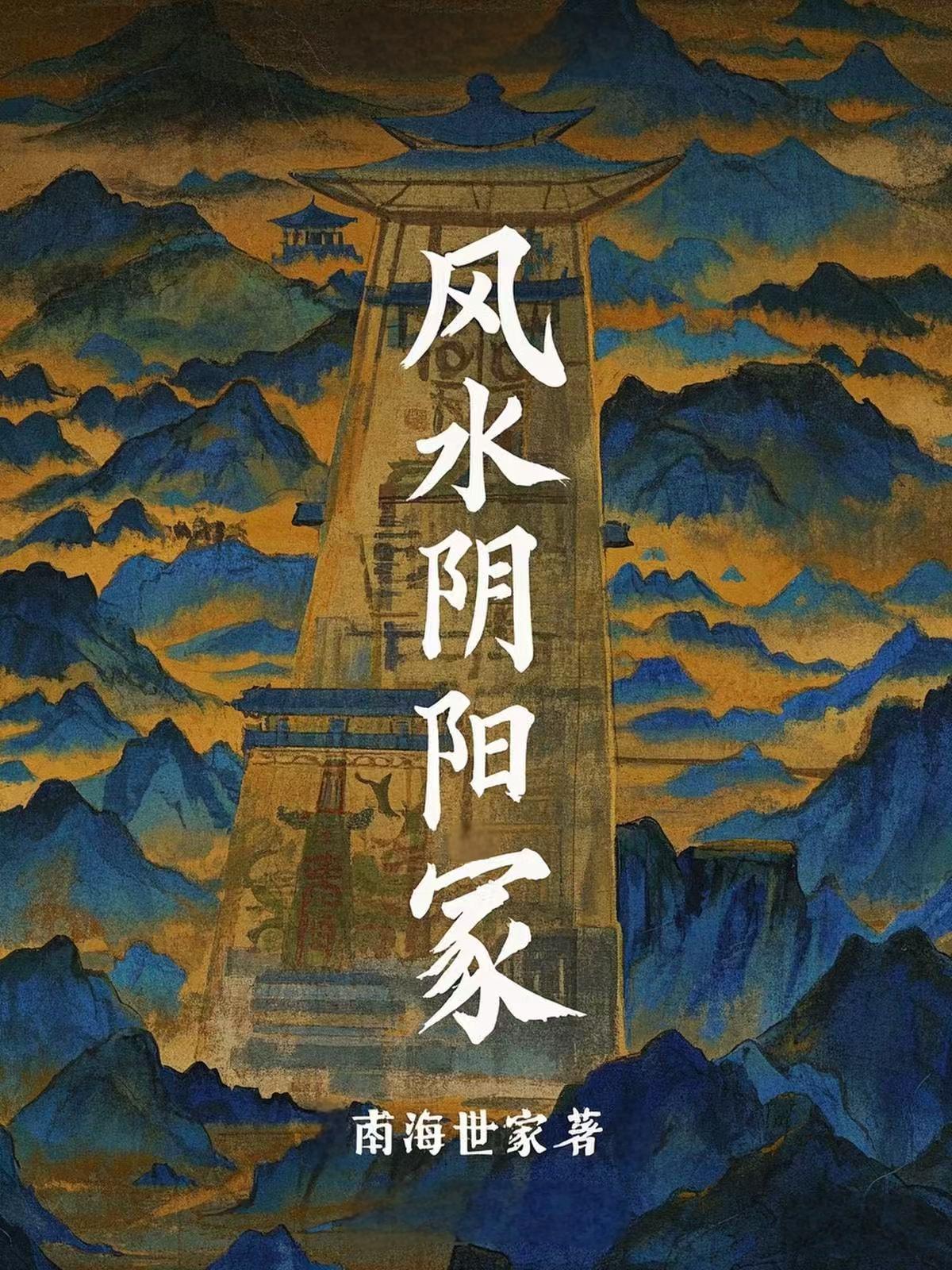
 南海世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7万
南海世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7万
夏夜的风裹着烧烤油烟掠过古城夜市,珩云蹲在塑料凳上嗦螺蛳粉,后颈突然炸起一片鸡皮疙瘩。三米开外的糖水摊前,穿黑西装的男人正用牙签扎破糯米糍,糖霜簌簌落进掌心。 "操,又是这帮孙子。"他猛灌一口冰豆浆,油汪汪的筷子精准戳中碗底的炸蛋。七个西装男呈扇形围拢,为首的正是在墓里被他用洛阳铲敲掉门牙的刀疤脸。 刀疤脸咧嘴露出镶金的牙:“珩老板,我们赵总请您喝茶。”

 贪婪的土豆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9.9万
贪婪的土豆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9.9万
言晶踩着七厘米的细高跟踏进别墅时,水晶吊灯忽然发出"噼啪"的电流声。她仰头望着晃动的灯穗,余光瞥见玄关处的貔貅摆件不知何时转向了东南方。 "言总,这位就是苏晨先生。"秘书小唐殷勤地引着个穿月白唐装的男人过来,那人指尖转着枚铜钱,在满屋子黑压压的丧服里活像只误入鸦群的丹顶鹤。 苏晨的丹凤眼扫过言晶锁骨间的翡翠平安扣,铜钱"叮"地弹向天花板。当那枚康熙通宝打着旋儿落回掌心时,他眉梢微不可察地跳了跳——卦象显示,这栋造价八千万的别墅,此刻正被某种活人忌煞笼罩着。

 春天的梦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74.9万
春天的梦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74.9万
肖雯雯是被一阵孩童的读书声吵醒的。 "母妃若是再装睡,儿臣就把您藏床底的梅子酒浇给御花园的牡丹。"脆生生的童音贴着耳畔响起,带着三分狡黠七分幸灾乐祸,“父皇说牡丹长势不好要砍花匠脑袋,不如试试醉生梦死疗法?” 她猛地睁开眼,对上一张粉雕玉琢的小脸。五岁男童穿着绛紫锦袍,腰间玉坠随着歪头动作叮当作响,那双与年龄不符的桃花眼正弯成月牙:“呀,诈尸啦!”

 草原孤狼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1.3万
草原孤狼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1.3万
我叫陆小天,是个抬棺材的。 这个职业可能很少有人了解。 从小到大,我都跟着爷爷一起做这个行当。 跟这些神鬼之事打交道,总是会遇到鬼,走夜路多了还能遇到鬼呢。 我又一次从梦中惊醒,想起了当年爷爷去世的时候,遇到的那些诡异的事情。 就算是到了现在,我也永生难忘,历历在目。 那天,爷爷刚出去给别人抬过了棺材,回来之后,突然就一头栽倒在地上,一病不起。

 女瞳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35.9万
女瞳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35.9万
夜色暗沉,阵阵阴风呼号,树叶在风中拍打着,那轮血色的月亮高悬在空中,将气氛晕染的有些可怖。 我打了个哈欠,趴在桌上有气无力的看着窗外,感觉有些无聊。 “七月半鬼门开·,又恰好碰上这么个天气。恐怕今晚上,是不可能有生意了,还不如早些收拾好东西,去休息呢。” 听到我这么说,母亲宠溺笑了笑,“好好好,我们收拾一下,这就去休息。” 我站起身来,准备帮母亲一起收拾。可还没等我有下一步动静,门外便传来了敲门声。

 糖糕糕 |
都市娱乐 |
完本 |
30.1万
糖糕糕 |
都市娱乐 |
完本 |
30.1万
柳州市第一人民医院,急救科病房外,人来人往。 李邵抱着膝盖蜷缩在角落,埋头失声痛哭。 “病人的的肿瘤已经恶变了,只有几个月时间了,你在拿不出三十万……” 主治医生冰冷的话一直在他脑中不断播放,就像一把尖锐的刀子狠狠地扎在他心头一般,疼得他快要窒息喘不上气了。 三十万的手术费,他根本拿不出来,这才是他崩溃的最根本原因。

 紫色燕尾蝶 |
古代言情 |
完本 |
33.3万
紫色燕尾蝶 |
古代言情 |
完本 |
33.3万
看着后面深不见底的悬崖,萧茉雨一袭黑衣,嘴角渗出鲜血,但是她还是露出了一抹冷笑,她回头看着面前的两人,眼中是满满的嘲讽:“没有想到,我最爱的人,居然会背叛我。” 闻言,权擎的眼中露出了冷漠,他缓缓答到:“茉雨,事到如今,你还是跳下去吧,你放心,你的祭日,我和璇璇一定会去给你烧纸的。” “就是啊,茉雨姐姐,你就跳下去吧,省的我们多费唇舌。”齐璇依偎在权擎的怀中,眼中是尽显得意。

 可珂 |
都市娱乐 |
完本 |
36.9万
可珂 |
都市娱乐 |
完本 |
36.9万
暮雨霏微的夏末,晚风萧索的凉着。 女人跌跌撞撞地一把拉开了车门,她步伐紊乱,气息急促,一张脸带着不正常的红晕,猛的拽过什么东西贴在自己脸上。 好冰。 好凉。 热……浑身热得厉害。 苏小沫只觉得自己像在蒸笼上的蚂蚁,热的浑身都在冒汗。 酒,一定是那杯酒。 自从喝下了那杯酒后,她就浑身不对劲。

 山葵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1.9万
山葵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1.9万
市局专案组,为了维护这座城市的安宁,成立的一年多以来,命案必破有案必追,成为了A市的一把利刃。 带领专案组的组长苏文霖成为了明星刑警,带领着专案组众人屡破其案,然而现在,专案组的人却焦头烂额。 法医周然蹲在散发着腐臭的垃圾桶旁,橡胶手套上沾着黏腻的液体。警戒线外晨练的老头正对着记者镜头比划:“这小区二十年没出过命案,肯定是外来人…”

 婉秋 |
古代言情 |
完本 |
53.7万
婉秋 |
古代言情 |
完本 |
53.7万
雨丝斜斜掠过长安城的青瓦,沈之禾蹲在潮湿的青石板上,指尖轻轻拂过尸体的咽喉。雨珠顺着她鸦青色的襦裙滚落,在积水中敲出细碎的声响。 "死者男,年约四十,身长七尺三寸。"她将银针探入死者口中,针尖霎时泛起诡异的靛蓝,“舌苔发绀,齿间残留苦杏仁气味——”

 九堡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6万
九堡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6万
冬夜的寒风呼啸,程仲缩了缩脖子,将衣服裹紧了一些,虎舍特有的腥臊味钻进鼻腔,程仲把最后一块鲜牛肉抛进铁笼,东北虎"大金"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,锋利的犬齿在月光下泛着寒光。 他是一名动物饲养员,已经做了快十年,一开始做是因为喜欢动物,但没有人知道的是,他有一种能够与动物沟通的特殊能力。

 随风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4.5万
随风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4.5万
灵堂里的长明灯忽然晃了晃。 三岁的苏倩文缩在阿爸的羊皮袄里,看着棺材底下渗出的水渍在青砖地上蜿蜒。那水透着股腥气,像是刚从冰窟窿里捞出来的鱼,在七月流火的夜里凝成细小的冰晶。 她的爸爸,是有名的棺材匠,手艺好人也老实,苏倩文在襁褓里就跟着他们出入各种白事,对这种环境早已习以为常。

 扬帆启航 |
都市娱乐 |
完本 |
58.7万
扬帆启航 |
都市娱乐 |
完本 |
58.7万
咸腥的海风卷着柴油味灌进鼻腔,林春燕把粗布围裙往腰后一系,抬脚跨过码头边泛着白沫的污水沟。天还没亮透,渔港的探照灯在薄雾里晕开毛玻璃似的光晕,早市上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声已经炸开了锅。 "靓女,新到的马鲛鱼要伐?"裹着胶皮围裙的渔贩掀开竹筐,银亮鱼鳞扑簌簌落下来。林春燕蹲下身捏了捏鱼鳃,指尖沾着新鲜黏液,“阿叔,这鱼鳃都发暗了,当我是第一天来捡漏?”

 河东河西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58.1万
河东河西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58.1万
梧桐巷的暮色来得特别早。 秦羽叼着半根油条蹲在门槛上,看最后一片夕阳从"雅藏轩"的鎏金牌匾上滑落。玻璃柜里那些青花瓷在暮色里泛着幽光,像一群沉默的观众。他打了个哈欠,后颈的纱布被晚风掀起一角——三天前那个混乱的夜,此刻还在隐隐作痛。 他抬手摸了摸头上的伤,为了生计不过是在古董店做个一个月拿两千块钱的小店员,凭什么自己要遭此横祸? 正为自己惋惜着,手机在裤兜里震起来,是老横发来的语音:“我说秦哥,真不用我陪你去医院复查?你后脑勺那伤看着就瘆人…”

 北冥有鲲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15.9万
北冥有鲲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15.9万
杭州的秋雨下得绵密,周谨言站在西泠印社旁的古董店二楼,指尖刚触到雕花木窗,一道惊雷突然劈开浓稠的夜色。玻璃窗上蜿蜒的水痕被闪电映得发亮,像无数条扭动的银蛇。 楼下传来三声闷响,不轻不重地扣在包铜木门上。他看了眼座钟,十一点零三分,这个时辰不该有客。转身时踢翻了青瓷笔洗,墨汁泼在波斯地毯上晕开狰狞的暗影。

 春天的梦 |
脑洞爽文 |
完本 |
50万
春天的梦 |
脑洞爽文 |
完本 |
50万
慕容衫被一阵刺骨的寒风冻醒时,发现自己正四仰八叉地趴在青石台阶上。她揉了揉磕得发麻的下巴,抬头就看见两个梳着双丫髻的小丫头正对着她指指点点。 “侧妃娘娘又摔跤了?” “嘘,她这身绿配紫的裙子,走路能不绊倒吗?” 慕容衫低头看着自己身上这件堪比调色盘打翻的襦裙,嘴角抽搐着抓住雕花栏杆爬起来。昨晚她还在手术室抢救连环车祸的伤员

 六斤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7.9万
六斤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7.9万
1925年秋,上海霞飞路的梧桐叶在暮色里簌簌作响。乔砚之裹紧灰呢大衣穿过街角,皮鞋踏碎霓虹倒影里的西洋广告画。街边报童挥着《申报》叫嚷日本纱厂罢工的消息,黄包车夫骂骂咧咧地撞开卖糖炒栗子的摊子,空气里浮着鸦片烟与雪花膏混杂的浊气。 "乔先生!"穿香云纱的茶楼伙计追上来,袖口沾着墨迹,“您订的《泰晤士报》到了,今早刚到的伦敦船货。”

 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6万
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6万
北风卷着雪粒子抽打窗棂,陆预缩在灶台前烤火,后脖颈突然挨了一记鞋底。父亲陆永贵佝偻着腰站在门口,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清单,棉袄上沾着棺木刨花的碎屑。 "小兔崽子就知道躲懒!"老棺材匠把纸条甩在儿子脸上,“赶紧去镇上置办五色纸钱、引魂幡,再捎两坛高粱烧回来。老孙头家明儿出殡,棺材还差最后三道漆。”

 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2.9万
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2.9万
雨丝在警戒线外织成银灰色帘幕,鹿珏转动着六阶魔方的手指突然停顿。警戒线内,穿着明黄色雨衣的鉴证人员像游动的萤火虫,在垃圾填埋场的腐臭中穿梭。她将魔方收进卡其色风衣口袋时,金属棱角硌到掌心尚未愈合的刀伤。 "组长,第三具了。"苏风风举着平板电脑凑过来,马尾辫扫过防毒面具边缘。屏幕上的三维建模图正在旋转,红点标注着三个抛尸点构成的等边三角形,“每次间隔十三天,这次是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