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0.1万
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0.1万
雨滴砸在锈迹斑斑的校门上,严嵩抬头望着"青岚特殊教育学院"的铜牌,潮湿的铁腥味里混杂着香灰气息。他攥紧背包带,指节泛白——这个动作能让他确定自己还活着,而不是游荡在孤儿院走廊的那些东西。 "202室。"生活老师递来的钥匙沾着暗红污渍,“记住宵禁后不要开窗。” 走廊尽头的宿舍门吱呀作响,霉味扑面而来。严嵩的右眼突然刺痛,这是凶灵靠近的征兆。四张铁架床贴着褪色符纸,靠窗的下铺床板上刻着密密麻麻的镇煞咒,咒文间凝结着黑褐色液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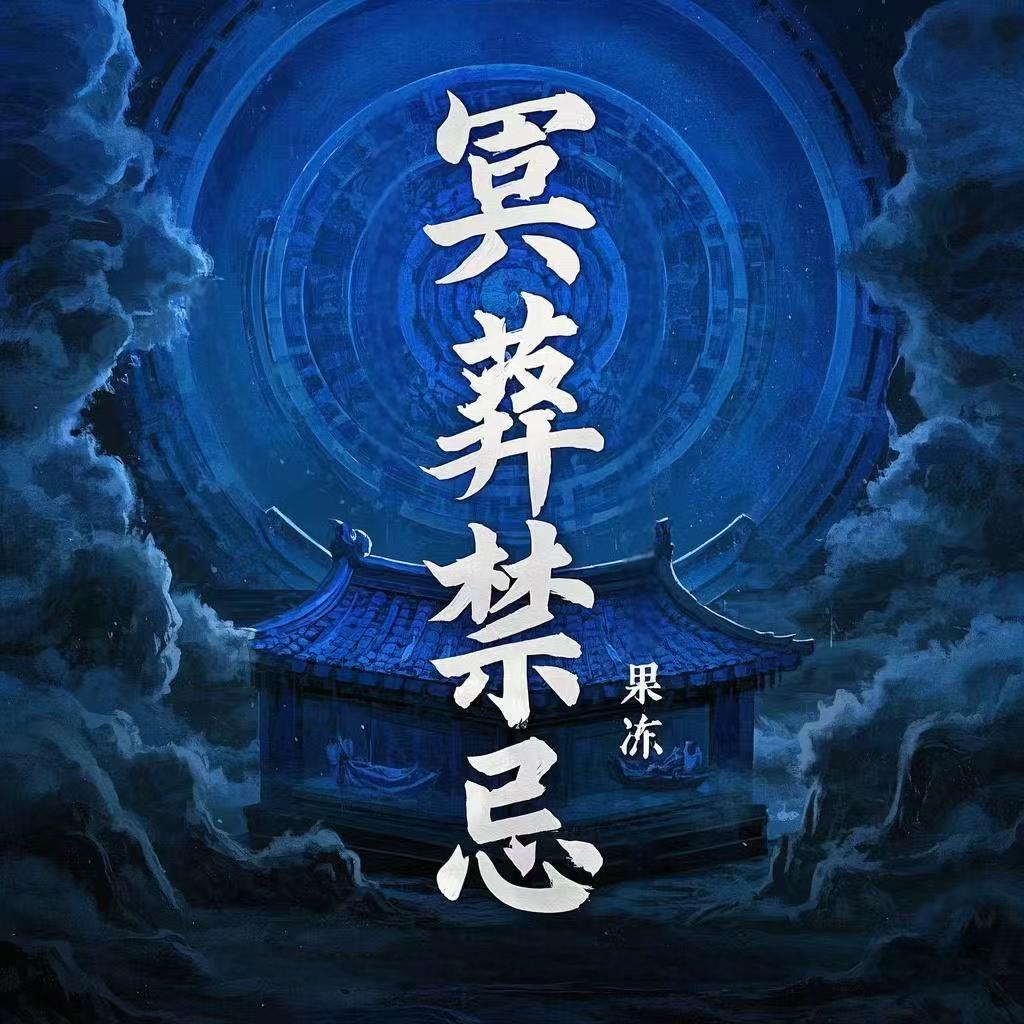
 果冻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1.5万
果冻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1.5万
雨点击打在玻璃窗上的声响被降噪麦克风过滤成细碎的白噪音,芮小小调整着环形补光灯的角度,看着直播间人数突破五万大关。她将垂落的黑发别到耳后,清冷声线在深夜格外清晰:“那双绣着并蒂莲的红绣鞋,就挂在教室后门的铁钩上。” 弹幕突然疯狂滚动起来,有人连刷了十个火箭礼物。芮小小瞥见置顶弹幕的ID叫"盛家藏古轩",金灿灿的VIP标识在深色背景里格外刺眼。她正要道谢,新的弹幕却让她的手指僵在鼠标上。 “主播印堂发黑,三日内必见血光。”

 步真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0.6万
步真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0.6万
法医台的无影灯在解剖室投下惨白的光晕,林畅的指甲掐进掌心。死者苏敏的腹腔像被暴力撕开的礼物盒,暗红血肉间赫然露出半截森白肋骨。 "这是第三根肋骨错位。"严峻宇的镊子夹起一团沾着粘液的纤维组织,"创口边缘呈现不规则撕裂,更像是…"这位素来冷静的法医突然停顿,喉结滚动两下,“内部爆破产生的压力。”

 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5.7万
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5.7万
教学楼的走廊在暮色中像条僵死的蜈蚣,周清数着第九盏忽明忽暗的廊灯,铜钱剑在掌心硌出深深的红印。中元节前的晚风裹着纸灰,把宣传栏里"禁止封建迷信"的告示吹得哗哗作响。 “救命…不要!” 尖叫声从三楼女厕传来时,他正盯着楼梯转角那滩暗红污渍。空气里突然漫开的血腥味让手腕上的五帝钱剧烈震颤,周清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台阶,帆布鞋碾碎满地碎玻璃,在月光下折射出无数扭曲的人影。

 下墓者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0万
下墓者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0万
我家后院有九座坟堆,埋着我娘和我八个哥哥。 我娘年轻的时候,在附近都是有名的美人,上门提亲的人把门槛都踏破了。 姥爷在我们那一片,是有名的看事先生。说我娘命硬,克夫克子,过了40岁才能改命。他这么一说,真就吓退了不少人。但还是有一些獐头鼠目之辈,并不死心。 隔壁村有个二流子叫沈峰,经常来家门前转悠,被赶跑了好几次,后来听说是她上乡里把姥爷给举报了。

 诸神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0万
诸神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0万
春意正浓的四月,阳光明媚而不燥热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,令人心旷神怡。二叔如常地躺在躺椅上,闭目享受着这温暖的日光浴。 自幼我便跟随二叔生活,他在我的心目中,就如同父亲一般的存在。为了不打扰二叔的安宁,我轻手轻脚地走到柜台前,悄无声息地从抽屉里取出几百块钱。今天下午,宿舍的几个兄弟已经约好外出游玩,而出游总是需要带些现金的。

 蜂蜜桃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0万
蜂蜜桃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0万
周宇从一阵剧烈的痛楚中惊醒,感觉到手心像是被火烧般的疼痛。头部沉重,仿佛被铁锤重击,脑袋里的嗡嗡声让他几乎认为自己的头要炸裂开来。眼皮沉重得像是挂上了千斤重锤,四周的嘈杂声,夹杂着人群的议论、掌声与呐喊,让他一时间难以适应。 慢慢地,他开始恢复一些意识,脑海中的迷雾渐渐散去。“这是哪里?”他心中疑惑。周宇试图说话,却发现嘴巴被胶布封住,无法发出声音。

 天宝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51.6万
天宝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51.6万
我的名字叫陈默,生于闽南陈家村,这个被九曲溪环绕的古老村落,藏着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禁忌。十八岁那年的惊蛰,父亲突然砸了供着祖宗牌位的八仙桌,在满地香灰里揪着我的衣领往门外拖。我至今记得母亲抱着门槛哭喊时,屋檐下的铜铃突然全部炸裂,碎碴子溅在青砖上像撒了一地血珠子。 "滚出去!没到卯年卯月卯日不许回头!"父亲把我推出院门时,手背青筋暴起得像要挣破皮肤。那扇贴着褪色门神的木门在眼前轰然关闭,我跪在爬满青苔的石阶上,听见里面传来碗盏碎裂声,还有妹妹细弱的抽泣。

 久久石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4万
久久石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4万
霓虹在雨幕中晕染成血色光斑,沈风将薄荷糖咬得咔咔作响。透过夜视望远镜,三楼窗口人影晃动,枪管在月光下泛着冷光。 "猎鹰报告,东南角发现自制炸药。"耳麦里传来爆破组急促的喘息,“引爆装置连着门把手,强攻风险太高。” 沈风舔了舔后槽牙,甜味混着铁锈味在舌尖炸开。三天前那具在护城河发现的浮尸还睁着眼睛,肿胀的指尖残留着蓝色油漆——和化工厂外墙如出一辙的孔雀蓝。

 金粉博士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1万
金粉博士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1万
法医的脚步声在走廊渐行渐远,陈晓暖站在单向玻璃前凝视审讯室。白炽灯下,那个穿着皱巴巴格子衬衫的男人正趴在审讯桌上打盹,额前碎发在空调风里轻轻晃动。 "第十七个。"她看着记录本上的编号轻声自语。刑警生涯里见过的嫌疑人多如过江之鲫,但这样在审讯室睡得毫无防备的还是头一个。监控录像显示这个男人在凌晨一点零七分冲进创意部办公室,浑身是血地跪在尸体旁边,而此刻他蜷缩的睡姿像极了误入捕兽夹的狐狸。

 酸葫芦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50.3万
酸葫芦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50.3万
鹭州的夏夜闷热粘稠,蝉鸣声在榕树荫里断断续续地抽搐。方明远抹了把额头的汗,手电筒光束扫过墙角的青苔,在斑驳的砖墙上投下扭曲的影子。这是他在"安家"凶宅拍卖公司工作的第三年,但推开这栋民国老宅大门时,后颈仍泛起细密的寒意。 "方哥,三楼阁楼的钥匙。"实习生小林递来铜钥匙,指尖在碰到他手掌时猛地缩回,“您有没有觉得…这里特别冷?”

 吕默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0万
吕默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0万
法医陈诺的手指在银色解剖刀上轻轻摩挲,解剖台上的白炽灯将死者脖颈处的淤青照得纤毫毕现。 林倩盯着那圈青紫色的勒痕,恍惚间仿佛看到二十年前父亲书桌上的案卷照片,那些泛黄的照片里,每具尸体的喉间都缠绕着同样的死亡印记。 "死亡时间昨晚十点到凌晨一点。"陈诺的声音像是从深水传来,"颈部舌骨骨折,机械性窒息致死。但最奇怪的是…"

 行云过月 |
古代言情 |
完本 |
22.3万
行云过月 |
古代言情 |
完本 |
22.3万
黑云压城城欲摧。 这是陈易水此刻的感受。 除此,她还感觉烦。 今天是周三,她休息,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洗了头,化了妆,穿上新买的小裙子,提着相机来到了京郊的免费公园。 没想到出来时还晴空万里,如今却乌云密布。 陈易水拍了一张乌云密布的天空,发了个朋友圈,配文:天要亡我。 她叹了一口气,装好相机,拔腿就往景区外走。

 清风子夜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9.7万
清风子夜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9.7万
在繁华的都市里,存在着一个似乎格格不入的小破屋。在这里面,住着一对男女,他们在这慢节奏地过着相当普通的日常。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…… “叮叮叮……”闹钟的响声打破了这里原来的寂静。 “傻瓜,起床上班啦!”赤雪匆匆起床,“再不起来就迟到啦!” “你才那啥……今天星期天!”萧雨轩吼完一头扎进被窝。赤雪一脸的木然,不过很快转回兴奋:“对了,今天是我生日!”

 大眼萌贼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50.1万
大眼萌贼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50.1万
“芊芊!”一个留着齐刘海的卷发女孩向着坐在电脑前的夏芊芊走了过来…… “干嘛?没看老娘正忙着了吗?”夏芊芊看都不看走过来的女生一眼,眼睛直直的盯着电脑的屏幕,右手控制着鼠标,左手还在键盘上不断的敲打着,整个人保持高度戒备的姿势,好像遇到了什么大麻烦一样。 “你怎么还在打游戏,早饭还没吃呢!”卷发女孩不满的看着盯着屏幕的夏芊芊,眼睛里面满是担心。

 富三代 |
武侠仙侠 |
完本 |
49.2万
富三代 |
武侠仙侠 |
完本 |
49.2万
冬去春来,江南云山之颠,似乎春天来得比其它地方更早一些,一望无际的草原,繁花锦簇,万紫千红,争妍斗丽,散发出浓烈的花香,使人有心旷神怡,无拘无束之感。仰望不远处群山起伏,大雪初溶,白湅仿如千万条银龙,射向碧绿的潭水中,如万马奔腾般向山下飞驰。其中夹着‘叮叮当当’的冰块碰击之声,加上百鸟齐鸣,好一首天籁之音。令人顿觉虚无漂渺,仿如置身在逢莱仙境之中,忘尽人间苦恼!

 侠客盗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7.3万
侠客盗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7.3万
山东诸城的一家小茶馆里,天南地北的人来这里胡侃,最近说的最多的也最传奇的无非是鬼眼唐朝,传闻此人年轻时做过摸金校尉,天生有一只阴阳眼,百鬼不侵,下斗盗墓得心应手,一生中摸过的冥器比一般人吃过的饭都多,可谓风光无限,可是在一天夜里,他却无缘无故的失踪了,有人说在他家的上方亲眼目睹有一条金龙徘徊,劈下了闪电,是盗墓太多遭报应了,也有人说,他在墓中盗出了一枚长生不老丹,吃掉以后得道升仙了,每次听到这些,我总是摇着头苦笑,他们说的都不是真的,没有其他人比我更了解唐朝了,因为,我就是唐朝。 ……

 折纸伞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50.1万
折纸伞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50.1万
花落凡尘莫寻依,楚天云瑶绕迷城 现世凄凉 又是一季炎夏,又是高考前夕。这个时候不只是空气闷热的让人透不过气来,更让人压抑的是到处弥漫着紧张的气息。 青蔓一中的校园里一个人影都没有,所有人都在教室里埋头苦读,学霸们在突破,学渣们在临时抱佛脚,只有一个人,例外……

 笙笙不惜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51.9万
笙笙不惜 |
玄幻奇幻 |
完本 |
51.9万
"下面有请国际著名新星歌手白依梦小姐为我们演唱<一眼万年>!"主持人激昂的声音回荡在演唱会广场内。 然后我穿着一身时尚最流行的紧身连衣裙,蹬着一双15公分的水晶高跟鞋,披着一头烫着大卷的棕色长发走向舞台。全场愕然,好一张绝世容颜。哈,没错本小姐正是白依梦。一曲完毕,我将s。h。e声音演绎的淋漓尽致,全场掌声一片,惊叹不已!

 天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0.4万
天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0.4万
宋仁宗年间,国家太平,边境安定,经济繁荣。史称“仁宗盛治”。 *** 九月初一。思远县。 思远县是靠近苗疆的边陲小城。 这个县城虽然靠近边陲却因了无战事,反倒成为了各国商人来往的重要商城,说大不大的规模却十分的繁华。 县官姓卢,四十岁上下,微胖的体型让人一眼看去如同面团一样,虽然有些糊涂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好官。但是若真的谈起这个县城第一个被提及的却是另一个人——捕头沈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