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风声水起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0万
风声水起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0万
我叫李山。 人人都说我是一个怪胎,因为我有三只耳朵。 我的右耳后面莫名其妙长了一个肉包,随着年龄的增加,和耳朵的形状越来越像。 去查了很多医院,都没办法查一个所以然出来。 我自小就能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,但每次回头都看不见人。 一直到村子里的一个姓胡的大师回来乐村,我才知道原来我这只“肉耳”叫鬼耳。 也就是说,我之前听到的那些声音,其实是鬼叫声。

 长须道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万
长须道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万
我叫张缺一。 就因为这个名字,从小上学的时候没被同学取笑。 我爷爷是有名的风水师,我的名字是他给我取的,是因为我命犯天煞,天生缺一。 自小我跟着爷爷一起长大,他教了我不少风水道术。 突然有一日,我爷爷失踪不见了,只留下一封信,指引我去叫一个叫宋山的人。 却没想到,送了宋家,正巧遇上有个大师正在抓鬼。 此大师名为周卫成,据说是天机门的传人,但对此宋家人是不信的。 我却信,因为我看到了他身上,专属于天机门传人的信物。 周卫成一看到我,打量了我好一会,才道:“同行啊...”

 红蜘蛛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8万
红蜘蛛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8万
今天刘雨宁邀请我到她家里,说是要带我去看房,我摸不着头脑虽然我和这位女警官的关系是不错,但让我去一起看房,这是什么意思啊? 我一时间有点疑惑。 我们在看房的时候,那中介带着我们到处转悠了很久,最后找到一个叫光华小区的地方,发现周围都是树木和庭院,还有许多商店和学校什么的,但小区里面特别安静,是个非常好的生活地方。 我们就义无反顾地选择这里了,中介那位先生礼貌地跟我们说这边的屋子都非常好,就是价格贵了点但对于刘雨宁这个白富美来说,这根本不算什么。

 寻梦江湖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0万
寻梦江湖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0万
“砰!” 一声枪响打破寂静,原本觥筹交错的宴会厅中,一片混乱。 “怎么回事?” “保安呢?” 原本沉寂在宴会中的众人,完全失去了冷静。 沈穆睁开眼,跳下床走到门边,将耳朵凑到门上。 他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动静很轻,似乎脚步声的主人想要刻意的隐藏。 “可算是来了!” 沈穆说着,拿出一个GPS监控仪。他伸手捣鼓了几下,可本该正常运行的监控仪,却根本就没有反应。 “罢工了?还是说对方刻意针对监控仪,做了准备?” 沈穆撇了撇嘴,将仪器丢到一边。

 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1.5万
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1.5万
“真相永远只有一个!” 叶梦心皱眉,作为警队十年来唯一一个女法医,被冠予了极高的名誉,更是使命使然,手里的动作不敢停下,可脑海中的剧情还是久散不去! 法医物证实验室的日光灯在凌晨三点依然亮得刺眼,叶梦心对着解剖台上的尸体皱了皱鼻子。死者后颈处有片指甲盖大小的皮肤呈现异常青紫,像朵被揉碎的矢车菊。 "顾队,你们刑警队现在都流行半夜送惊喜?"她戴上乳胶手套,金属解剖刀在指间转了个漂亮的银花,“这姑娘的尸斑都还没完全固定,死亡时间不超过三小时吧?”

 金粉博士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2.1万
金粉博士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2.1万
夏末的暴雨将槐树中学染成铅灰色,林深握着转学通知书站在校门口,雨水顺着伞骨在肩头洇开深色水痕。他仰头望着爬满藤蔓的牌匾,"槐"字右侧的鬼字旁被铁锈侵蚀得支离破碎。 "新同学?"清脆的女声穿透雨幕,扎着双马尾的女生突然从保安亭后探出头。她校服领口别着银质八卦镜胸针,右手握着根缠满红线的桃木棍,“姜小满,灵异社社长。要帮忙搬行李吗?” 林深后退半步,行李箱撞在湿漉漉的槐树根上。树干凹陷处嵌着半截红绸,被雨水泡得发黑的绸布上隐约可见"永镇"二字。"不用了,谢谢。"他转身时瞥见教学楼拐角闪过白影,像件飘动的校服衬衫。

 果冻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5万
果冻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5万
清晨的雨丝斜斜划过警徽浮雕,淦商商站在市局刑侦支队办公室窗前,看着玻璃上蜿蜒的水痕与自己的倒影重叠。法医苏俊推门进来时带起一阵消毒水味,她下意识将父亲送的钢笔往记事本内侧挪了挪。 “商商姐,西郊化工厂的尸检报告。”二十三岁的年轻法医递来文件夹,白大褂袖口沾着暗褐色痕迹,“死者指甲里的纤维组织与嫌疑人毛衣完全吻合。” 钢笔在指尖转了个圈,淦商商刚要开口,手机突然在桌面震动起来。范言和的号码在屏幕上跳动,她接起电话时听见刑侦队长急促的呼吸声:“商商,立刻带人来牡丹街32号。”

 风流大官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6万
风流大官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1.6万
阴雨连绵的六月,檐角滴水在青石板上凿出深浅不一的凹痕。裴砚用麂皮绒擦拭着博古架上的定窑白瓷碗,忽然听见卷帘门被拍得哗啦作响。 “裴老板!有急货!” 门外站着的快递员浑身滴水,黑色雨披下露出半截靛蓝工装。他怀里抱着个缠满保鲜膜的包裹,雨水顺着塑料膜滑落,在门槛前积成一滩浑浊的水洼。裴砚注意到那人左手小指戴着枚古怪的铜戒,戒面浮雕的饕餮纹被绿锈蚀得面目狰狞。 “劳驾放寄存柜。” 他隔着玻璃门比划电子屏,“扫码支付——”

 两簇拟墨葬祭凜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00万
两簇拟墨葬祭凜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00万
宁静的夜晚,小虫子都不在发出了声音,夜晚的黝黑给人有一种吞噬的感觉。 只有街上的老式路灯散发出一点黄昏的光芒。 从远处传来了一阵脚步声,由远到近。 “啪嗒,啪嗒,啪嗒”类似水滴在地上的声音不断的出现。 正在这片地区巡逻的警卫,听到了这声音,他听说,这附近经常闹鬼,他不想去看情况。 但是也没办法。 巡逻警卫拿着手电筒,小心翼翼的向着那个方向走去,时不时的回头看下,但每次看都看不见什么东西。

 铁血炮灰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8.2万
铁血炮灰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8.2万
我叫王小峰,生于九九年,从记事起最喜欢听的就是爷爷的故事。 爷爷的故事虽然千奇百怪,但所有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憋宝。 憋宝,不在三百六十行,属外八行中偷盗门中的一支,北方又称牵羊术。 从事这个行当的人,被称为憋宝人。 憋宝人行走于深山远海之地,潜伏于市井街巷之间,凭借自己独特的手法和器具,夺天地之造化,寻万物之精华。 憋宝人眼中的宝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说世间罕见,甚至是闻所未闻。 而且,有些宝贝存在极为特殊,所以,憋宝人有时甚至需要出入各种绝地秘境,秘野仙踪。

 剑指南山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2万
剑指南山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2万
我叫郑天官!之所以有个如此土得掉渣的名字,还要从我的爷爷说起! 我老郑家祖孙三代都居住在封京尉县的一个乡镇之下的穷村庄里,名叫——刘集! 说是隶属封京,实则过了村西便属中州,过了村南便属昌都,如此位置,也就不可避免的造就了村子三不管的局面!也恰恰是因为这三不管之地,才引得我爷爷定居在此,只从这村名便可知晓,我爷爷乃是外来人口,至于爷爷以前是做什么的,以及我老郑家祖上的来历就连我父亲和叔伯也不知晓,爷爷也从未说过,不过据我推测,爷爷以前应该是个不寻常之人!

 贪婪的土豆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7.7万
贪婪的土豆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7.7万
秋雨裹着寒意砸在青石板上,苏童缩了缩脖子,油纸伞骨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。他蹲在王家祠堂的滴水檐下,指尖摩挲着掌中那枚磨得发亮的六壬式盘。雨水顺着祠堂飞檐的嘲风脊兽淌下来,在青砖地上洇出九道蜿蜒的沟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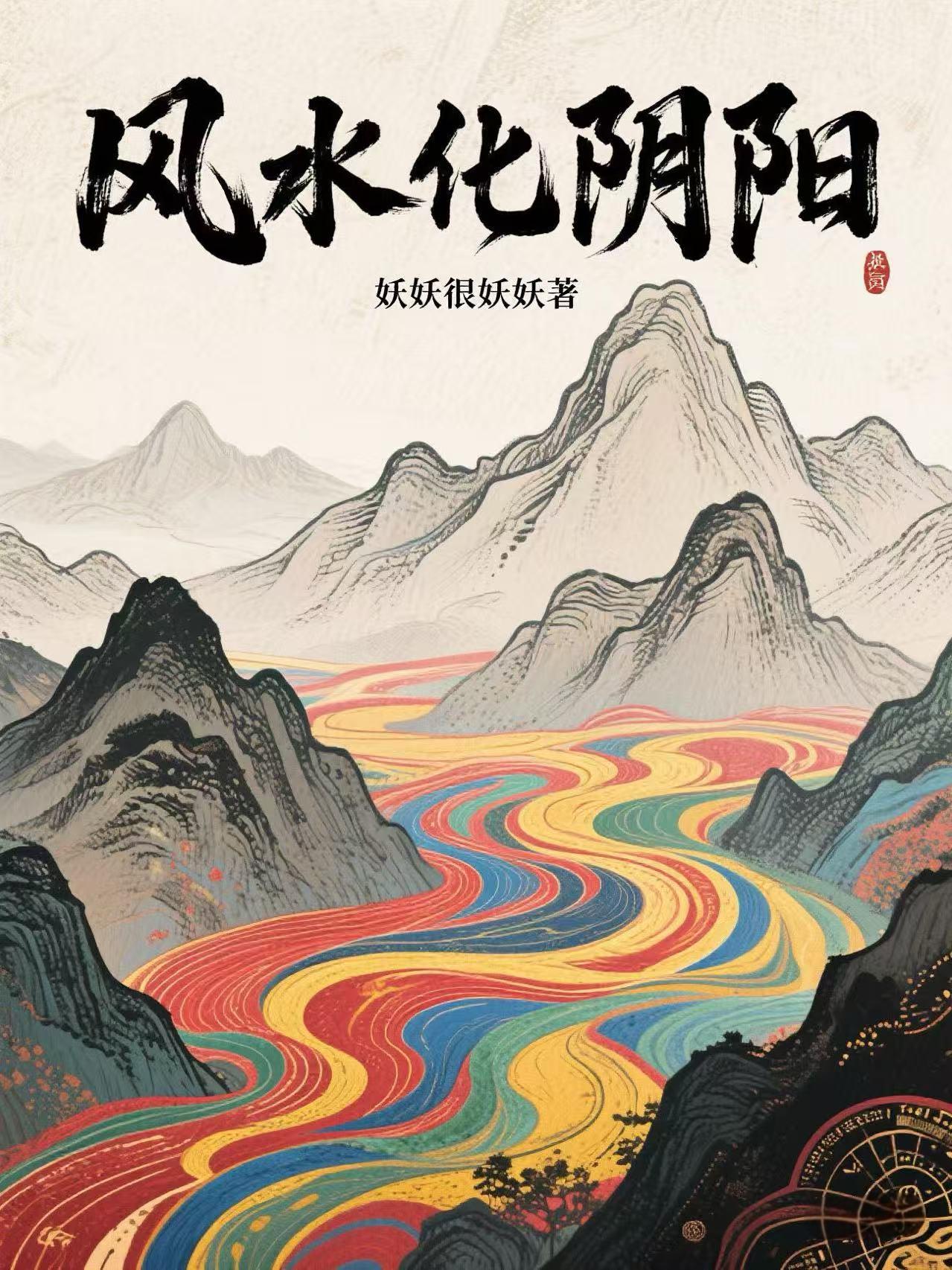
 妖妖很妖妖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0.3万
妖妖很妖妖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0.3万
卿若然骑着小电驴在乡间土路上颠簸时,后座捆着的黄纸元宝簌簌往下掉。她一脚蹬住快要散架的三轮车,丸子头上沾的柳叶随着动作晃了晃,扯着嗓子冲前面带路的周家侄子喊:“你们村狗都成精了是吧?追我三条街了!”

 云峰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0.8万
云峰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0.8万
晏临霄蹲在酸枝木茶台前,指尖捻着枚生锈的铜钱在烛火上翻烤。檀香混着普洱的陈味在古董店里浮沉,玻璃柜台里错落摆着几尊鎏金佛像,日光斜斜切过门楣,将"玄枢斋"的匾额映得半明半暗。 "晏老板,您给掌掌眼?"穿条纹polo衫的中年男人抹了把额头的汗,从公文包里掏出个红绸包裹。绸布揭开时带起细微的铜腥味,晏临霄眉梢微动,余光瞥见那枚双鱼玉佩沁着层诡异的青晕。 铜钱在烛焰里发出"滋"的轻响,晏临霄突然松手,看着烧红的钱币坠入茶海。水汽蒸腾间,男人手边的普洱泛起细密涟漪。"黄泉渡,阴阳错。"他拎起紫砂壶续茶,壶嘴悬在杯口三寸处顿住,“王先生最近…常做溺水的梦吧?”

 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8万
紫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8万
法医陈子姗推开沾着晨露的警戒线时,解剖刀在证物袋里反射出冷光。九月的朝阳穿过破碎的玻璃窗,在高三(7)班门牌上切割出明暗交界线,那里挂着半截被扯断的“优秀班级”锦旗。 “死亡时间约在昨夜23点至凌晨1点。” 她单膝跪地,医用橡胶手套擦过地砖缝隙, “这里有拖拽痕迹。” 血迹呈喷射状在讲台蔓延,浸透了摊开的数学课本第三十二页——正讲到概率论基础。

 千年一剑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5.7万
千年一剑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5.7万
林分握着鸡毛掸子扫过博古架时,木雕貔貅突然翻了个跟头。八月的蝉鸣混着朝天门古玩市场的喧闹涌进小店,老式吊扇在头顶发出苟延残喘的吱呀声。 "见鬼了?"他伸手去扶那尊清代木雕,指尖刚触到包浆温润的雕工,柜台上的招财猫突然"啪嗒"一声摔了个倒栽葱。玻璃珠做的猫眼在水泥地上骨碌碌滚到门槛边,正巧被刚进门的胖子踩个正着。 "林子!你丫又在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?"王铁柱拎着两杯奶茶踉跄站稳,圆脸上还挂着空调房带出来的汗珠,“我妈让你今晚去家里吃火锅,说是给你驱驱邪气。”

 清虚道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4万
清虚道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4万
秦岭山区的暴雨来得毫无征兆。 黄豆大的雨点砸在越野车顶棚上,发出密集的鼓点声。林砚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发紧,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疯狂摆动,却怎么也擦不净瀑布般倾泻的雨水。后视镜里,考古队的白色面包车像只笨拙的甲壳虫,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挪动。 林砚原本是个考古专业的普通学生,原本以为假如真正的考古队还需要很长时间,但是一周之前,推荐他进入考古专业的老前辈却突然来找他,将他引荐给了考古地负责人。

 雪雾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2万
雪雾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2万
明德路夜市漂浮着孜然与油烟的浊气,霓虹灯牌在暮色中次第亮起。苏砚心将褪色的蓝布铺开,青铜罗盘压住布角,三枚磨损严重的开元通宝在掌心轻轻碰撞。 她抬眼望向天际,暮色中的贪狼星泛着诡异的青芒。这是《星枢密要》记载的"贪狼噬月"之相,每当此星异动,必有古墓现世。街角传来烤鱿鱼的滋滋声,混着游客的嬉笑,却掩不住她腕间星月菩提突然发出的细碎颤音。

 玄念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6万
玄念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80.6万
林忘尘蹲在宠物美容室的玻璃门前,食指和中指夹着的烟灰已经积了半寸长。他歪着头看笼子里那只正在啃磨牙棒的柯基犬,突然咧嘴一笑:“胖墩儿,你屁股这么圆,要是做成驴肉火烧能切八片不?” 柯基犬的磨牙棒"啪嗒"掉在笼底。 "小林!"店长从二楼探出头,地中海发型在吊灯下泛着油光,“给雪纳瑞剪指甲的客人等半小时了!”

 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08万
老朝奉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08万
沈墨蹲在客栈二楼的木栏杆前,指尖的烟灰簌簌落在青苔斑驳的石阶上。远处群山在暮色中化作起伏的兽脊,山坳里飘荡的雾气正悄悄漫过青石板路,将檐角挂着的铜铃笼上一层惨白。这是他们被困在落魂坡的第三天。 木质楼梯突然传来密集的脚步声。穿着靛蓝布衫的客栈老板端着油灯上来,昏黄的光晕在他脸上割裂出深浅不一的阴影,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直勾勾盯着走廊尽头的客房——三天前考古队的四个学生就住在那间屋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