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0.2万
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0.2万
A市最著名的国际酒店,原本悠闲显贵的气氛变得渐渐急躁起来,来往的车辆停下就迅速离开。 大堂经理此刻急得满头大汗,不停的用手帕擦自己的脸颊。 顶层,彰显着崇高身份的精致房间内,却散发着阵阵腐朽气息。 法医老陈的橡胶手套在浴室瓷砖上擦出细微响动,祁晟宇站在玄关处深深吸气,鼻腔里漂浮着血腥味与蓝山咖啡的醇香。他抬起手背蹭了蹭鼻梁上的金丝眼镜,镜片后的目光扫过270度环形落地窗——天鹅绒窗帘严丝合缝,遮住了正午刺目的阳光。

 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0.1万
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70.1万
雨滴砸在锈迹斑斑的校门上,严嵩抬头望着"青岚特殊教育学院"的铜牌,潮湿的铁腥味里混杂着香灰气息。他攥紧背包带,指节泛白——这个动作能让他确定自己还活着,而不是游荡在孤儿院走廊的那些东西。 "202室。"生活老师递来的钥匙沾着暗红污渍,“记住宵禁后不要开窗。” 走廊尽头的宿舍门吱呀作响,霉味扑面而来。严嵩的右眼突然刺痛,这是凶灵靠近的征兆。四张铁架床贴着褪色符纸,靠窗的下铺床板上刻着密密麻麻的镇煞咒,咒文间凝结着黑褐色液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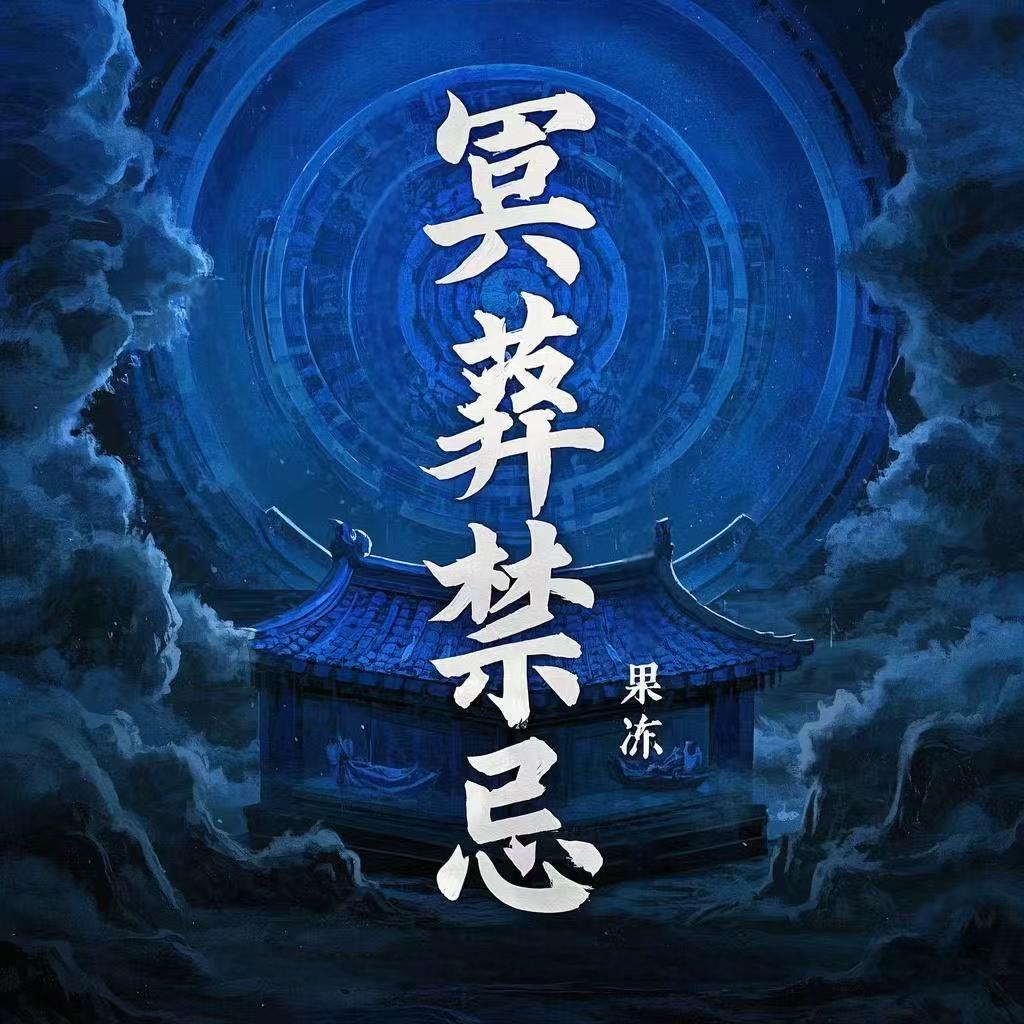
 果冻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1.5万
果冻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1.5万
雨点击打在玻璃窗上的声响被降噪麦克风过滤成细碎的白噪音,芮小小调整着环形补光灯的角度,看着直播间人数突破五万大关。她将垂落的黑发别到耳后,清冷声线在深夜格外清晰:“那双绣着并蒂莲的红绣鞋,就挂在教室后门的铁钩上。” 弹幕突然疯狂滚动起来,有人连刷了十个火箭礼物。芮小小瞥见置顶弹幕的ID叫"盛家藏古轩",金灿灿的VIP标识在深色背景里格外刺眼。她正要道谢,新的弹幕却让她的手指僵在鼠标上。 “主播印堂发黑,三日内必见血光。”

 步真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0.6万
步真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0.6万
法医台的无影灯在解剖室投下惨白的光晕,林畅的指甲掐进掌心。死者苏敏的腹腔像被暴力撕开的礼物盒,暗红血肉间赫然露出半截森白肋骨。 "这是第三根肋骨错位。"严峻宇的镊子夹起一团沾着粘液的纤维组织,"创口边缘呈现不规则撕裂,更像是…"这位素来冷静的法医突然停顿,喉结滚动两下,“内部爆破产生的压力。”

 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5.7万
天宝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5.7万
教学楼的走廊在暮色中像条僵死的蜈蚣,周清数着第九盏忽明忽暗的廊灯,铜钱剑在掌心硌出深深的红印。中元节前的晚风裹着纸灰,把宣传栏里"禁止封建迷信"的告示吹得哗哗作响。 “救命…不要!” 尖叫声从三楼女厕传来时,他正盯着楼梯转角那滩暗红污渍。空气里突然漫开的血腥味让手腕上的五帝钱剧烈震颤,周清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台阶,帆布鞋碾碎满地碎玻璃,在月光下折射出无数扭曲的人影。

 下墓者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0万
下墓者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0万
我家后院有九座坟堆,埋着我娘和我八个哥哥。 我娘年轻的时候,在附近都是有名的美人,上门提亲的人把门槛都踏破了。 姥爷在我们那一片,是有名的看事先生。说我娘命硬,克夫克子,过了40岁才能改命。他这么一说,真就吓退了不少人。但还是有一些獐头鼠目之辈,并不死心。 隔壁村有个二流子叫沈峰,经常来家门前转悠,被赶跑了好几次,后来听说是她上乡里把姥爷给举报了。

 诸神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0万
诸神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0万
春意正浓的四月,阳光明媚而不燥热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,令人心旷神怡。二叔如常地躺在躺椅上,闭目享受着这温暖的日光浴。 自幼我便跟随二叔生活,他在我的心目中,就如同父亲一般的存在。为了不打扰二叔的安宁,我轻手轻脚地走到柜台前,悄无声息地从抽屉里取出几百块钱。今天下午,宿舍的几个兄弟已经约好外出游玩,而出游总是需要带些现金的。

 蜂蜜桃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0万
蜂蜜桃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0万
周宇从一阵剧烈的痛楚中惊醒,感觉到手心像是被火烧般的疼痛。头部沉重,仿佛被铁锤重击,脑袋里的嗡嗡声让他几乎认为自己的头要炸裂开来。眼皮沉重得像是挂上了千斤重锤,四周的嘈杂声,夹杂着人群的议论、掌声与呐喊,让他一时间难以适应。 慢慢地,他开始恢复一些意识,脑海中的迷雾渐渐散去。“这是哪里?”他心中疑惑。周宇试图说话,却发现嘴巴被胶布封住,无法发出声音。

 久久石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4万
久久石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4万
霓虹在雨幕中晕染成血色光斑,沈风将薄荷糖咬得咔咔作响。透过夜视望远镜,三楼窗口人影晃动,枪管在月光下泛着冷光。 "猎鹰报告,东南角发现自制炸药。"耳麦里传来爆破组急促的喘息,“引爆装置连着门把手,强攻风险太高。” 沈风舔了舔后槽牙,甜味混着铁锈味在舌尖炸开。三天前那具在护城河发现的浮尸还睁着眼睛,肿胀的指尖残留着蓝色油漆——和化工厂外墙如出一辙的孔雀蓝。

 金粉博士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1万
金粉博士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9.1万
法医的脚步声在走廊渐行渐远,陈晓暖站在单向玻璃前凝视审讯室。白炽灯下,那个穿着皱巴巴格子衬衫的男人正趴在审讯桌上打盹,额前碎发在空调风里轻轻晃动。 "第十七个。"她看着记录本上的编号轻声自语。刑警生涯里见过的嫌疑人多如过江之鲫,但这样在审讯室睡得毫无防备的还是头一个。监控录像显示这个男人在凌晨一点零七分冲进创意部办公室,浑身是血地跪在尸体旁边,而此刻他蜷缩的睡姿像极了误入捕兽夹的狐狸。

 吕默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0万
吕默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0万
法医陈诺的手指在银色解剖刀上轻轻摩挲,解剖台上的白炽灯将死者脖颈处的淤青照得纤毫毕现。 林倩盯着那圈青紫色的勒痕,恍惚间仿佛看到二十年前父亲书桌上的案卷照片,那些泛黄的照片里,每具尸体的喉间都缠绕着同样的死亡印记。 "死亡时间昨晚十点到凌晨一点。"陈诺的声音像是从深水传来,"颈部舌骨骨折,机械性窒息致死。但最奇怪的是…"

 清风子夜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9.7万
清风子夜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9.7万
在繁华的都市里,存在着一个似乎格格不入的小破屋。在这里面,住着一对男女,他们在这慢节奏地过着相当普通的日常。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…… “叮叮叮……”闹钟的响声打破了这里原来的寂静。 “傻瓜,起床上班啦!”赤雪匆匆起床,“再不起来就迟到啦!” “你才那啥……今天星期天!”萧雨轩吼完一头扎进被窝。赤雪一脸的木然,不过很快转回兴奋:“对了,今天是我生日!”

 侠客盗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7.3万
侠客盗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7.3万
山东诸城的一家小茶馆里,天南地北的人来这里胡侃,最近说的最多的也最传奇的无非是鬼眼唐朝,传闻此人年轻时做过摸金校尉,天生有一只阴阳眼,百鬼不侵,下斗盗墓得心应手,一生中摸过的冥器比一般人吃过的饭都多,可谓风光无限,可是在一天夜里,他却无缘无故的失踪了,有人说在他家的上方亲眼目睹有一条金龙徘徊,劈下了闪电,是盗墓太多遭报应了,也有人说,他在墓中盗出了一枚长生不老丹,吃掉以后得道升仙了,每次听到这些,我总是摇着头苦笑,他们说的都不是真的,没有其他人比我更了解唐朝了,因为,我就是唐朝。 ……

 天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0.4万
天一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0.4万
宋仁宗年间,国家太平,边境安定,经济繁荣。史称“仁宗盛治”。 *** 九月初一。思远县。 思远县是靠近苗疆的边陲小城。 这个县城虽然靠近边陲却因了无战事,反倒成为了各国商人来往的重要商城,说大不大的规模却十分的繁华。 县官姓卢,四十岁上下,微胖的体型让人一眼看去如同面团一样,虽然有些糊涂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好官。但是若真的谈起这个县城第一个被提及的却是另一个人——捕头沈括。

 暗修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4.2万
暗修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4.2万
深夜,夜空里挂着昏黄的毛月亮,山林里偶尔传来几声夜猫子凄厉的叫声。。一群疲惫的人,踏着沉重的脚步,还在奋力的在漆黑的深林里赶路,队伍最后跟着一个已经累的气喘吁吁的半大小子。他就是我的爷爷:鲁有财。 我爷爷鲁有财,十二岁以前家里是个大户,就是人们常说的地主。十二岁那年,我太爷爷过世,太奶奶一个女子,缠斗不过家族的兄弟长辈们,原本属于自己的财产,都被族人用各种理由和借口弄走了,不消半年,家里就被掏得干干净净!

 花姑姑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5.8万
花姑姑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5.8万
我叫方小诺,正方形的方,大小的小,诺言的诺。是个保险业务员,身高一米六,体重八十,特长是——见鬼。 从我有记忆以来,我时常能看到这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,它们围绕在我周围,昼伏夜出,神出鬼没,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的正常生活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能看见它们,它们又为什么找上我,世界上那么多人,为什么偏偏只有我?

 秀玲珑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28122
秀玲珑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28122
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,流传在百信中的民间故事可谓不胜枚举。它们有的已被科学所解释。我们今天要将的这个故事,正和一个人们口儿相传的神秘现象有关,它就是——鬼压身……

 闯天下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42522
闯天下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42522
你相信这世界有那些东西的存在吗?当你有意识无意识的碰触到那些灵异的现象,你还会抱着可笑的科学模样来鄙夷这所谓的封建迷信吗?在张俊石记忆的深处清晰的记得这样一副画面,那是准备参加高考的前几天,母亲陈可花带着他去拜仙,张俊石家在东北农村,母亲带他拜的仙不是庙观里那些日日吃着香火的菩萨和老道,跟他们相比要寒碜的多,他所拜的仙连一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。

 山精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58649
山精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558649
2014年6月3日凌晨3时13分,一串紧密的电话铃声响起,打破了深夜的宁静,让这静谧的时光变得紧张,仿佛预示着将要到来的暴风雨。

 一念浮屠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05290
一念浮屠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605290
“什么!我已经结婚了,老婆还是一个女鬼!” 是巧合还是上天的安排,被的抛弃的远坤寒遇上极品女鬼,是外挂被开启,还是天生背负着不一样的命运,在美女如云的世界看的远坤寒如何登上仰望之颠。